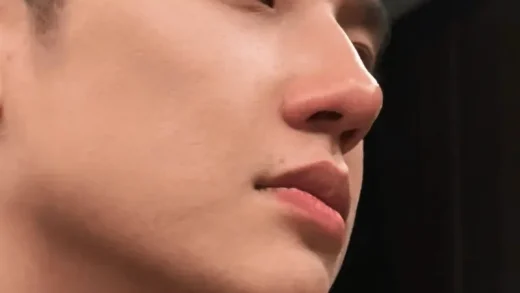我是想知道这理由是什么,我想看着他的眼睛,让他告诉我。
我挂了电话,茫然地向着灯塔的方向走。
天已经渐渐地暗下来了,在我的脑子里反反复复只盘旋着一句话“我只需要一个理由了,一个分开的理由,有一个理由我就走开。”
到我站在大可宿舍的门口的时候,大可仿佛预感到我要过来似的,他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书,呆呆的眼神正好与门口的我相遇。
“能说下为什么吗?”
站在离他们航标站的院落不远的一块空地,我问。
我也不知道自己希望有一个怎样的答案,不知道能有什么样的理由能让我选择离开他。
站在眼前的大可似乎要比前瘦了很多。冬装在他的身上变得像是没有以前那样合体,那个曾经在河边的水泥台上挥舞着树枝比划着信号旗“我爱你”动作时的身影,仿佛已经沧桑了很多。
夏日河边阳光。
冬夜山上灯塔。
只是一转眼间,怎么就恍如隔世?
63
“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
对着眼前的大可,我又说。
其实我的追问能让他收回他说过的话吗,如果不能,知道一个理由又有什么意义?我的大脑在那个时候已经变得呆滞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怎么做。不知道应该接受他的选择,还是挽留。我又该怎么挽留。心里已经是那种歇斯底里的感觉了,但却要保持着和他一样的沉默。
大可像是刚刚在电话里一样,什么都没说。
过了许久,他像是对我又像是对自己说:
“没有为什么。我只是不想那样了,我觉得那样不好,我想好好复习考学。”他没有对着我,而是看着远处的灯塔,像是很坚定地回答。
我只是不想那样了。
我觉得那样不好。
我想好好复习考学。
这也是我所能想到的他唯一能够让我无话可说的理由。无论爱还是不再爱,如何继续还是不再继续,有一个底线我知道,那就是我不能自私,我不能够置他的前途于不顾。这是唯一一个能够让我选择离开的理由,而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也恰恰是这个理由。我还能说什么呢。
大可仍然看着那山顶的灯塔在夜晚放射的尤为耀眼的光芒。
我无法看到他说话时的眼神,但我想既然这话已经说出来了,必定是他自己的选择了。
我想,我应该走了。
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怎么说,只能安静转身,远离。
“丛彬……”
我已经走开了一段距离,他叫住我。
“对不起。”他对着我的后背说。
这也许应该是我要说的呢,或许他根本和我就不属于同一类人,如果按照他说的他觉得那样不好,他不想那样,那么,只能说是我将他引入歧途。相对于他或许是非同志的主流生活,相对于他的军校梦与前途,我的放弃或许是唯一能再为他做到的。
我没有回头再说什么,因为我不敢回头。
大可像一直和我保持着距离走在我后面,送到了山口,他像是停住了脚步。
他在我身后远远地说,“丛彬,你一个人要好好的……”
那一刻,夜色中的我泪雨滂沱。
像什么东西从我的身体里抽走了一样,我成为一个空壳。在山路上的夜色里,我一个人走着,像一只飞蛾,独自承受着扑火之后灼伤与痛楚。
我拿出手机,看存在里面的每一条大可的短信,我都能想象得到他写短信的表情和我收短信时的欣喜。我认真地看短信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似乎那便说明了大可什么分手的话都没说,他仍与我在一起。
但我知道,这一切终究是不存在了,我的手机的屏上永远不会再跳来那个让自己心跳的名字。也许我们一起去买的这手机已然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我认真地每一条每一条地打开短信看,然后每一条每一条地删去。
山路上的石头将我绊倒,但我毫无知觉地爬起来,捡起地上的手机,继续走,继续看,继续删。
收件箱空了,心也空了。
64
最后把他的名字和号码也从手机里删去,可是那个号码已经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里,我怎样从记忆里删掉这个号,删掉他的名字,删掉我们在一起的所有点点滴滴,在一起的每一个让我觉得不再孤独觉着幸福的往昔?
如何删去记忆呢?
也许把我从世界上删去,一切才会真正地归于虚无。
我没想过,死亡在那一刻变成那么美好的事情。
那一刻,像是在寒冷的街头遇到一团暖暖的火,烘烤着你的冰冻的心,让你慢慢走入,慢慢融化到那一团火当中。又像是在黑暗当中发现一丝微亮的光,你的整个世界也只有那一束光在你的眼前,你虔诚地接受着牵引,聚精会神地向着那光,走向另外一个世界。
走出那个山脚不远的海滩,就有着那样的一团火与光,召唤着我专注地走过去,走进海水当中。
那种感觉是特别奇异的,明明严冬,海边腥涩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在我脚下的海水却是暖暖的,湿热的,越向前走,寒冷就少一些,暖热就多一些。在我脑海中所有的记忆都消失了,所有的悲欢离合在一瞬间了无踪影。我忘了我,忘了我身边的这个世界,我全部感觉与思维都集中在脚下温热的体验当中,我的鞋,我的小腿,我的膝盖,隔着贴在身上厚厚的冬季水兵服,我一点点地沉入那无边的暖热里。慢慢的,沿着这种感觉,我的思维又开始复苏,似乎所有温暖的记忆都来自于脚下。我像是回到了童年,在那样寒冷的夜晚,睡前与爸爸妈妈挤在一个木制的盆中泡脚,妈妈的脚心在温水中踩着我的脚背,爸爸的目光看着我和妈妈,爸爸他在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