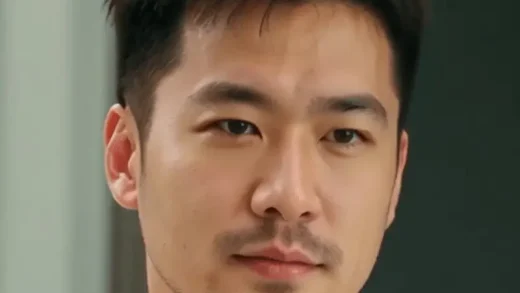“嗯。”
余大可表情复杂,像那种面对难题无从下手的困顿。
突然觉得两个人站在甲板上这样说话似乎有些不方便,而且和我和他本来就是两个不同部门的,两人单独在这儿窃窃私语,总让人瞅着怪怪的。
我说还是去那个舱室坐一会儿吧,我有话跟你说。
余大可未置可否,想了想,还是答应了。
舱室好像被文书整理过,放烟头的瓶子不见了,并且他把书堆往里挪了挪,椅子在书的后面,书堆前面有一小块空间。
余大可一进屋就走到那书堆前面,像是要和我保持距离似的。
“干嘛,怕我非礼你啊?”
“丛彬,以后咱们别开这种玩笑了。”
我坐到书堆后的椅子上,看着仍然站立的他。他有点不自然地从书堆上拎下一摞书,也坐下来。
我们隔书而坐。
“你觉得那天晚上我有些变态是吗?”我直奔主题,或许对于一个不与我属于同一类的人而言,这个词更能直达他内心所想要表达的。
“也不是,不能这么说,也有我不对的。”
“你有对不对,这根本就没什么对不对的好吧。你不是一直想听我以前的事吗,现在还有兴趣吗?”
在余大可渐渐不再躲闪的眼神当中,我开始了我的叙述。
“那天我跟你说过,不喜欢女生,好像从小就是,其实自己真正肯定这一点,是我上大学之后的军训,遇到一个比我小一岁的男孩,他姓严。我从他们宿舍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他了,真的,说不清为什么,反正看到他就觉得亲切,熟悉,觉得特别高兴。
“在我们军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和他一起站岗,那天晚上就跟前两天与你在舱室一样,我们从来都没样过,是他的第一次,也是我的第一次。”
“靠,第一次,听着这么别扭——我还是呢!”
余大可的眼神恢复了那种单纯,他在认真地听着我说,在说这一句话的时候表情有一点滑稽,不过我没理会他,继续说。
“那天晚上之后,我们走得更近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喜欢彼此,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的。不管是训练,还是后来的上课,只要有对方在,我们就会觉得特别开心。我在学校的广播站给他点那首他喜欢听的歌,我们一起去图书馆,我们一起去另外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城市里玩,时间过得像飞一样。”
“挺难得的,跟兄弟一样,后来呢?”
余大可或许是被我的叙述感染了,坐在那摞书上,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后来我妈病了,病得很严重。我妈只有我,她希望我早点结婚,那时候恨不得没毕业就去结婚,实现我妈的愿望,给妈添个孙子,在医生说了她的病情之后,这种想法更强烈了,我不想让我妈伤心,她太苦了。”
余大可掏出烟,衔在嘴上,点燃,但他没抽,却从嘴上拿下来,递给我,我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就从他手上接过烟,衔到自己的嘴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吐了出来,那蓝色的烟雾像一个不规则的圆,在我们之间袅袅升起。
他自己也点燃一支,顺手从地上捡起一张废纸,叠成折子状,放在我们中间,用来接烟灰的。
“因为你妈的原因,你和你那同学分开了?”余大可问我。
“嗯。”
“靠,你想过没有,你这个原因根本站不住脚嘛。”
“我不知道。后来妈妈还是去世了。我就记得严陪我一起回了一趟老家,从老家回学校的火车上,我咬住他的肩痛快地哭了一场。回到学校之后,我就一下子什么也记不住了。”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我从大学报名参军,进了部队。”
“就再也没有与他联系过吗?”
“没有了。”
我想到严在寄来的我没有拆开的那封信,那个在海中漂远了的飘流瓶,但这个我没跟余大可说。
“你应该再联系他的。”余大可有些黯然地说。
“都快三年了,就是联系上了,也是物是人非,天各一方,又有什么意义呢?”
余大可没再接话,我和他一起陷入一种无边的安静当中。
“丛彬,咱们也做这样的好兄弟吧?”
余大可突然打破安静,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
我的心头掠过一阵感动,接着听他没说完的话。
他又点燃了一支烟,想是鼓起很大勇气一样。
“操,刚才你说你军训时候看到严的那种感觉,我也有,真的,知道吧,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个鸟人,就是你在给文书出板报,你站在黑板边上有点发呆的样子。当时我就在想,这哥们儿我难道以前在哪里见过吗?你一直那么冷冷的样子,不好接近,不过还好,给你画了个刊头,就成兄弟了。”
“你那次跑医院去看我,心想这非典大家躲都来不及,搞得我心里挺感动的,当时我就在想怎么着都要拿你这个深沉当好兄弟。”
“但是……”
“但是那天晚上之后,你就觉得咱们做不了好兄弟了是吗?”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