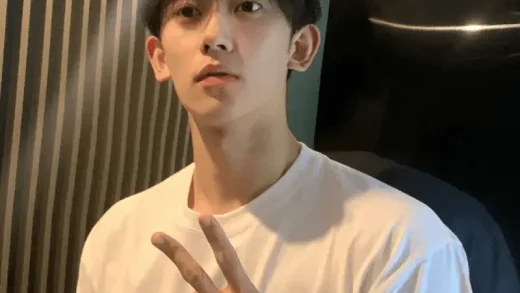就是那一夜,我和伟静静坐在顶楼。当朝阳从对面楼房的背后跳出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阳光下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
于是我便有些急着想离开这座城市了。
我走的时候没有人到机场送我。
伟曾经提出来,但我拒绝了。我走的那天,佳慧应该是去美国领馆签证吧。我于是对伟说,你不要送我了,还是去陪她吧。
他点点头。
这些都发生在那个清晨。我们一起从我家的顶楼上走下来。
我们只见了那一面。很久很久的一面。因为整整一夜,我们共同坐在顶楼,直到太阳升起来。
然而,我们的告别却非常简练。仍旧如同两个不期而遇的近邻,聊尽兴了,分手各做各的去了,丝毫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况且,他不是说过吗?很快,我们就常在一起了。
接下来的一周,除了必须办的事情,我便独自留在家里。小莲已经回乡下老家了。
我原本是要整理一下家当的。
那些杂物仍然堆在那里,只是体积又膨胀了不少。
又忆起儿时,我曾独自在那些杂物堆里寻觅。我原本是希望和楼下的孩子们一起嬉戏的,尽管他们曾经抢走我的塑料宝剑和玩具冲锋枪。
然而,父亲把我独自锁在家里。
想着想着,我便不愿意动手清理这些杂物堆了。谁知道我会不会又从中发现些什么呢?
直到临走的一天,我默默地锁上大门。
屋里的一切还如一周前一样。
我拖着手提箱,登上出租车。司机问我去什么地方。
我原本是要去机场的。可此时,脑海中却一下子涌出好多好多地方:
清华园,
圆明园,
卧佛寺,
美领馆,
但下意识地流出口来的,却是紫竹院。
车子于是驶上二环路。
为什么会想到美领馆呢?为什么会说出紫竹院呢?我问自己。难道,又是那本日记在作祟了吗?
如今,我已失去了父亲,却仍旧不能忘记那本日记吗?难道,我仍旧还在憎恶着伟吗?
我连忙叫司机把车直接开往首都机场。
我闭上双眼,把头埋在手掌里。我是如此的无地自容了。
想必那出租车也曾从古观象台前经过。不过这次我却错过了。于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列车从那下面缓缓驶过。
17
走出海关,隔着层层的接机的人群,我看到阿文。
他正奋力地挤过来,迎着我,辟出一条狭小的通道来。
底特律机场的秩序原本不是这样混乱的。不过,当有航班从亚洲飞来时,就另当别论了。
隔着人群,他注视着我的眼睛。他的眼神里充满焦虑。
我不曾告诉过他我何时回美国来。我只告诉他,也许要离开两三个礼拜。回程的时间要根据情况而定。
我突然回忆起,我曾说过会发email给他,告诉他回来的日期。
然而,在北京的时候,我却忘记了。
况且,我也不知道,在北京何处是可以发email的。短短的一周,除了必须要做的事情,我都静静地坐在家里,面对着几堆似乎已经面对了一个世纪的杂物堆。
莫非,他送我的时候,已经仔细察看过机票了?没有接到我的消息,他便还是按照机票上的回程日期赶了来?
我有些感动了。
他额边挂着一滴汗水,鼻梁上的黑色细边眼镜也有些歪斜了。我于是微笑起来。
他隔着人群大声地问我家里是否一切都好?他脸上的焦虑散去了,又换做少年般的笑容。
他果然还是个孩子。然而我的微笑,原本代表着别的意思。
我的微笑有时的确是虚伪的。比如此刻,它并不代表快乐的心情。此刻我其实是麻木的。麻木的人是不应该有任何表情的。不知从何开始,我已经学会了微笑。
可阿文还是孩子,他并没有学会微笑。他微笑,因为他的心里的确释然了。
他终于走到我面前,终于发现我袖子上的黑色丝绸的标志了。
他的微笑便立即消失了。他伸出手握住我的胳膊,握得很紧很紧。
他似乎要说些什么,却不知从何开口。我本想继续微笑,打破僵局。可突然间,我却笑不出来了,我竟然丧失了微笑的本事了。
而且,更糟糕的事也发生了。我似乎也同时丧失了忍住泪水的本事。我的眼眶里已经饱盈了。
难道,我又要把脸贴向他的面颊么?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够掩藏起来那马上就要涌落的泪水。
他的眼神在灼着我。
不可以。我告诉自己。在飞机上,我下过决心。我要把阿澜的日记丢掉。因为父亲曾经告诉我:小冬,毕业,成家。
小冬,毕业,成家。
我于是又有了些勇气,又找回了微笑的本事,也找回了忍住泪水的本事。
我微笑着对阿文说:谢谢你,阿文。咱们走吧。可很大的一滴泪水,还是落下来了,很重很重地落在机场光滑平坦的地板上,迸裂了。
我却仍然微笑着。我的鼻子并没有抽搐。我的表情应该是自然的。然而,阿文却紧紧注视着我。他的眼睛也微微发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