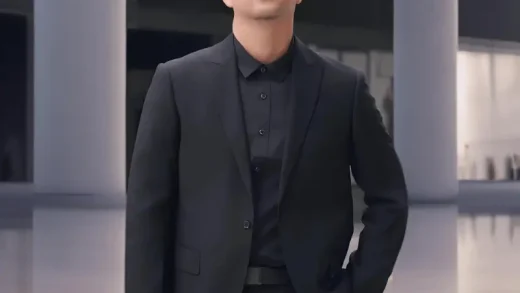我的师傅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冯师傅,我们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冯扒皮。据说解放前他出生在地主家庭,满脑子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思想,我们师兄弟四人分黑白两班,轮流伺候这个老家伙,可还是不能让他满意,总是能鸡蛋里挑骨头似的抓到毛病,一旦被他抓到不认真干活,轻则被骂,重则就会被罚推煤。
尽管如此,但这份工作对我来说还是来之不易的,我十分的珍惜,盼望有一天能够像师傅一样成为一名正式的“司炉工”。就算不能在总厂上班,至少也可以到分厂去烧烧锅炉,养活一家吃饭连供憨子上学应该是不成问题。
我怀抱着如此渺小的愿望咬牙坚持着,但生活对我的考验并没有就此结束。
憨子上了初中之后变得越发的调皮,逃学旷课成了家常便饭,甚至还趁我上夜班的时候夜不归宿。而赵立新也是变本加厉,每天除了喝酒耍钱就是躺在炕上睡大觉,我每月工资一共是105块,留下20块钱其他全部交给萍姨用来养家,虽是如此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大不如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忽然传出萍姨怀孕的消息。
萍姨今年已经42岁,一直不曾怀孕,我虽然不清楚内情,可是我看得出来,她的怀孕还是在计划之内的,毕竟赵立新这段时间安稳了不少,晚上不再纠缠萍姨,我和憨子也算能睡个好觉了。
俗话说:曲木违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这个赵立新就是条披着人皮的狼。
春末夏初季节,我下夜班回家,家里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只有赵立新一个人躺在炕上鼾声如雷蒙头大睡。我一身的疲惫,用冷水在院子里擦洗身体。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早年的工厂内是有公共浴池给工人们洗澡的,但由于我下夜班比较早,所以浴池还没有开门,所以只能带着一身的煤灰渣子回家用冷水擦洗,这已经是我下夜班要做的第一件事了。
清晨的阳光并不能使我感到温暖,我只能用那冰冷的毛巾使劲的摩擦自己的身体,借此缓解由内自外的寒冷。就在此时,我身后的房门突然被推开了,赵立新似笑非笑的靠在门框上看着我。他只穿了一条棉布的花裤衩,松松垮垮的裤衩内高高耸起一个小帐篷。
我讨厌他这个人,更讨厌他猥亵的笑容。我抓起衬衫披在身上,接着去抓长裤,可就在这时赵立新忽然闪到我身后,一把将我抱在怀里,同时把手伸进我的短裤内,打手揪住我的要害,我浑身一阵痉挛似的疼痛。
他嘴里骂道:“小杂种!看见我你跑什么跑?我还能吃了你!”
“我……我没有!”我身体疼痛,含糊的说:“你……你撒开我!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哼哼!”他嘲弄似的在我耳后撕咬我的耳垂,一字一顿地说:“我要干你!”
一想起上次痛苦的经历,我就忍不住双腿打颤,心里又急又气,用尽全身力气挣扎,试图摆脱他的控制。面前的水盆被我踢翻在地,铁盆掉在地上的声音惊动了邻居的看家狗,发出“嗡嗡”的犬吠。
“妈的!小杂种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给脸不要脸!”他手上猛一用力,我当时疼的面无血色,就连喊声都没有发出来。
没等我从疼痛中解脱出来赵立新已经把我半拖半架的带进了卧室,他轻轻一甩,我就像个包袱一样被摔在炕上。我想抵抗,可从小腹处传递来的疼痛感使我连腰都直不起来,只能佝偻着身子卷在炕上。
别动我小弟(15)
我是一条丧家犬,自己的伤口自己舔;
面对无情的嘲笑,眼泪全往肚子里咽。
我是一条丧家犬,不需要同情和可怜;
面对凛冽的寒风,谁能给我片刻温暖?
多想回到妈妈身边,那里是美丽的家园,
多想回到爸爸身边,那里是避风的港湾。
原来那只不过是一场梦,
梦中我睡在你的怀抱,你轻轻抚摸着我的脸,
鲜花绽放在蓝天,笑容流动在眉宇之间;
没有痛苦纠缠,也没有世态变迁,苦也是甜。
一切的一切,都留在那个梦里面,
梦醒之后:我还是一条丧家犬……
“平子,平子!醒醒,你怎么睡在这儿了,会着凉的!”我迷迷糊糊的睁开双眼,视线涣散,脑子一片混乱。我也下意识的问自己,我在什么地方?这个人是谁?
正在我发呆的时候,那人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哎呀!怎么这么烫啊,你发烧了!快点,我带你去卫生所。”
那人伸手抓住我的胳膊,我忍不住“啊”的一声抽回手臂,疼痛使我清醒了不少,我看清了眼前人的相貌,不是别人正是王凯。
“平子,怎么了?快让王叔看看!”说着话他要来抓我的胳膊,我下意识的闪开,低声说:“没,没事,我没事。”
环顾四周,此时我坐的地方是工厂里的小凉亭,我的记忆一点点的回到脑子里,在被王立新施暴之后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力气,竟然走回了工厂,后来就依在这座凉亭里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看这时候的时间想必已经是中午了,我大概睡了有三个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