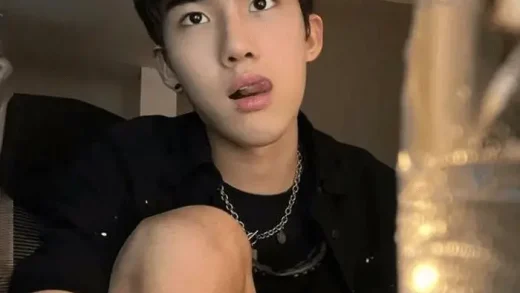春节来临之前,亮子妈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事情来的太过突然,我得知消息赶到医院的时候并没看见她最后一面,我只看见萧东双眼通红,站在医院大门口的电话亭拿着电话破口大骂:“……你这个王八蛋……你一走十几年不回来,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肯回来?我爸死了,你妈也死了……难道你要等到我也死了你才肯回来吗?你是不是个冷血动物……你到底在想什么……难道这里就真的不值得你留恋,连……连回来看一眼都不行吗……”
骂着骂着他就哭了,电话机脱手掉落在一旁,而他哭的却是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嘴里有气无力的叨咕着:“我没什么对不住你的……你为啥要一走那么多年都不回来……”
我拾起电话,听到的是亮子在大洋彼岸的哭泣。那一刻我才真正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爱情”和“爱”字相比虽然多了一个情,却显得轻薄许多,情之一字,绵绵如春之细雨,夏之凉风,纵然无孔不入,细致入微,却不如“爱”字来得强烈,火热,激昂澎湃,气势磅礴。爱是发之于心,情是动之于念,只有有了爱,才会有情。他们的爱已经超越了“爱情”的束缚,世俗的羁绊,这才是真正的爱,不用海誓山盟,却足矣刻骨铭心!
葬礼因为要等亮子回国一直拖延了7天,灵堂就设在我叔叔家中,平时不见来往的三姑六婆,四叔二大爷都专程赶了回来,亮子唯一的一个舅舅全权主持,俨然已经成为了这个家的下一任主人。
萧东对这个舅舅没有什么好感,这几天他一直负责招待外地亲友的食宿问题,他们家的月亮大酒店几乎成了专用的食堂。那天下午萧东刚把头一批亲友送到饭店,我和憨子为明天出殡做准备,就在这时门口忽然有人喊:“亮子!你可回来了!”随后人声嘈杂,有的叫“叔”有的叫“舅”有的叫“外甥”有的叫“大侄子”。
按照预先的约定亮子应该今天凌晨到达东北,没想到他比计划中的提前了7个半小时。说话间亮子被众人簇拥着进了卧室,他戴了一副茶色太阳镜,穿了一件白色紧身型棉服,下身配一条水蓝色牛仔裤,手里只拎了一个随身的小皮箱。
为了显示自己的办事能力,亮子的舅舅逐一向亮子介绍屋子里所有的亲戚,亮子每个都是点头回应,始终未发一字。
等大家陆续介绍完毕就开始七嘴八舌的说了起来,焦点都围绕在国外的生活上,更有甚者竟然把六七岁的孩子推到亮子面前,问亮子能不能把他带出过去。亮子依然用生疏的,甚至是轻蔑的微笑回应,然后把头转向我,问:“平哥,我妈的灵堂在哪?”
亮子的态度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人群中已经有人沉下了脸,但还是有人附和着亮子说:“对,对,对,应该先去看看你妈,给她上柱香!”
这间屋子是原本的厨房间壁出来给亮子住的,现在被改成了临时的灵堂,北面的屋子光线昏暗,一盏“长明灯”两支蜡烛给原本阴冷的屋子更增添了几分诡异。亮子的舅舅推门进去,讨好似的从供桌上拿起了三支香,正要点燃,亮子忽然开口说:“我自己来!你们出去吧!”
这话一出又让那些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亲戚们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亮子的舅舅更是满面通红,亮子自己从桌子上拿起三支香点燃,恭恭敬敬的举过头顶,然后跪在母亲的遗像前磕了头三个响头。
“是不是他回来了?”他问。
我把目光落在那扇紧闭的房门上,萧东两步就抢到门口,抬手就要推门,看就在他的手即将触在门板上的时候,他忽然停止了动作,他几次试图推门却都没下得了手,最后只能颤抖着扶住门框。
众人面面相觑的看着他,就在这时,房门开了,亮子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换了一件素白的汗衫,摘掉了墨镜,他的眼眶中盛满了泪水,慢慢的顺着眼角滑落。
亮子突然开门倒让萧东有些措手不及,二人对视一眼,萧东立刻转身,头也不抬的朝门口疾走。
“哥!”亮子轻声喊了一声,“我回来了!”
萧东顿住脚步,依然没有回头,哽咽的说:“你……你好好休息一下吧……我……我还有事……先走,先走了……”
说完萧东一路飞奔下了楼。
等我和憨子追到楼下,发现萧东一个人趴在方向盘上哭泣。
就在萧东大哭不止的时候,忽然又女人在我身后说:“这是怎么了?跑到楼下哭什么?”
与此同时萧东的女儿萧冉跑到萧东跟前,大喊:“爸爸,你怎么了?”
萧东立刻用袖子擦干眼泪,抬起头看见我身后抱着孩子走来的高月不耐烦的说:“你怎么来了?”
“妈让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所有我就来了。你怎么在这儿哭上了?还没到发丧出殡的日子,留着眼泪明儿个再哭也不晚啊……”她的语气半讥半讽,半真半假,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