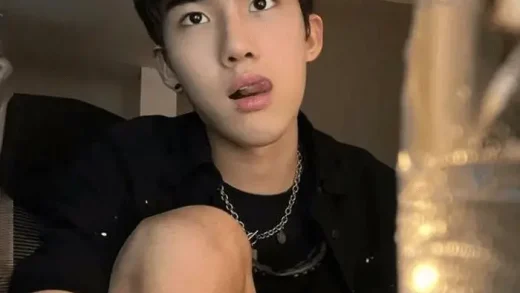酒喝到一半,石卓小心地问何飞:“你们俩……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何飞看了看石卓,怔了半天不知道从何说起。
断断续续总算讲出了前因后果,何飞看看石卓,他正望着自己微微笑着。
“我真想不明白,到底什么是问题,至于这么严重!”何飞说着,心中不免烦躁,扬起脖子灌了一大口酒。从舌根到腹腔,如同有团火焰,一边灼烧一边路过。
“要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其实问题也不算小。”石卓说。
“知道你丫是个强人,没你不明白的事儿,你就别他妈的卖关子了!”
“项磊吧,开始接触的一段时间你会感觉倒他一身骄傲,再接触一段时间,能掏心窝子给你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家伙骨子里妄自菲薄极了!他对我说过,他深知自己这点秉性,所以他常常对自己信任的人倾诉些什么,希望在得到认同的过程中锻炼自信。当然他倾诉的东西不可能完全对,但他同样容易被说服,你没发现他是一个没什么主见的人吗?”
何飞一脸茫然地摇摇头。
石卓笑笑,继续说:“当你说服他之后,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坏结果。所以当他严肃地对你表达某种心情的时候,你要么认同他,要么说服他,这对他相当重要,别以为保持沉默或者不痛不痒地回应两下就等于让着他了,对他来说,我敢肯定,不认同就等于全盘否定,不尝试说服就等于不在乎。比如他对你说起那些亲人的境况时,很容易从你的反应中发现你根本不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当然,共鸣是强求不来的,他正是因为确信这一点,才觉得和你之间没什么希望。他这个人,最不喜欢不纯粹的东西了。”
“其实那天看到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之后,如果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或是对他说句‘都过去了别瞎想了’,或许也不会闹起来。”何飞叹道。
“就算那天不会,迟早有一天也会。”石卓坚定地说。
何飞点点头:“操!也是!”
“说真的,我们不是农村长大的,也许真的不能真切地体会到像项磊这样从农村过来的人他们的想法,也就是基于人性里与生俱来的那么一点儿善,在看到他们身处悲苦境地时,至多去同情一下,而且只是对这个庞大群体中少数被我们发现的人们诸多悲苦中的一小部分,而且还只能是时不时地触动那么一小下,稍微面对更多人的更多悲苦境遇、稍微再频繁一点或者坚持得再久一点,大概就生厌了。”石卓说。
何飞紧锁眉头,若有所思。
“这家伙其实是一个头脑复杂但言行简单的人。说你们没有出现大的问题是因为他身上的大问题其实很容易被你解决掉。”石卓笑道。
“真的吗?”何飞看着石卓,希望得到最终确认。
“你自己去试试不就知道了?”石卓继续笑道,“不过,我觉得南京那件事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你所料想的那么无所谓,而是你室友这件事比起那件事来说,也许更适合他借以表现自己乱七八糟的情绪罢了。你仔细去看看这家伙用心写过的东西,就能发现他的情绪从波澜不惊变得乱七八糟有多么的容易了!哈!”
何飞想了想说:“你知道吗?我从南京回来对他坦白之后,他问我和他在一起是不是仅仅出于这段时间养成的一种习惯而已……”
石卓笑得更欢了:“那你觉得我有可能养成这个习惯吗?我至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地对任何一个人拍着胸脯说,我可不是什么习惯都能养成的。——所以,那件事他没说什么,不代表他心里无所谓,他大概是觉得委屈了你,自己有情绪也不好发作。”
何飞举起酒杯碰了一下石卓手里的杯子,不无认真地说:“妈的!像你这种人,怎么就混到我们这个学校里来了!”
“别提这茬了!考不上北大是兄弟这辈子永远抹不平的一道疤,这都几年前的事儿了啊!现在什么时候听人说起高考,什么时候还他妈的隐隐作痛呢!”石卓笑着说。
两个人很快就干掉了一斤白酒,石卓提议再叫一瓶的时候,何飞慌忙喊停。这醉意正恰到好处呢,再多可就大了,何飞尚有打算,需要留存足够清醒的意志。
“老石你打个电话问问项磊干什么呢,现在。他可能不会接我电话。”何飞说。
石卓嘿嘿一笑,拿出手机拨通了项磊的电话。
“说刚洗完衣服,这会儿正在东门口的印务室里办点事儿!”
石卓诡秘地笑笑,说自己要去学校南门等杨琳,于是两人出了小饭馆儿就地道了别。
何飞呼出一大口酒气,定了定神,然后大步迈开朝学校东门走去。
项磊正在印务室里排队,何飞远远地看到了他的侧脸。
一时间构思不好相遇的最佳方式,何飞索性没有走近前,绕进印务室对面的卫生院里,倚在卫生院门口的树上,点上了一支烟。这个角度,项磊出了印务室无论左拐还是右拐都不会发现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