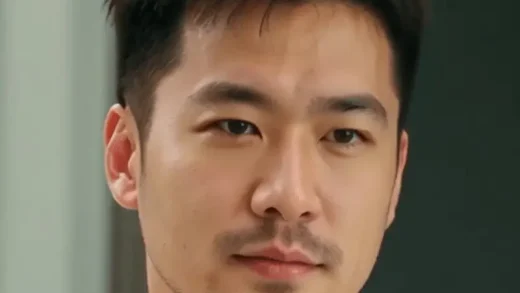我先把张云的那些毒品藏起来,暗暗观察他的反映。张云一连几个星期都没有什么反应,我总是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检查他那个抽屉已经家里能藏东西的地方,一看到那些袋装的粉末啊,摇头丸之类的就全部给他拿起来。张云这个不求上进的家伙,一肯没看过《谁动了我的奶酪》,不然他自己也可以写本《谁动了我的毒品》。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我是在帮他,想我修炼了两千多年,一直没能得到升天,可能是公德未满吧,如果能救张云出苦海,说不定就功德圆满了呢。
我继续在家翻箱倒柜的找张云藏的毒品,然后自己私藏起来,不知道张云是没发现还是怎么的,一直没找我谈话,我藏的毒品越来越多,多得连我自己都有点害怕了,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北京的夏天终于在几场沙尘暴之后姗姗来迟,我特别喜欢夏天,可以穿得花枝招展的,和姐姐,Danny在三里屯招摇过市。也可以和Danny一起去团结湖游泳,然后肆意的看那些公0们搔首弄姿的卖弄自己D罩杯的胸肌。或者去柳浪游泳,柳浪真的是个GAY的据点,在里面游泳的男的都是GAY,女的都是拉拉,穿着各式性感的泳裤,尽情的卖弄风骚,Danny口口声声说自己喜欢胖子,但是看到身材好的帅哥就两眼发直,这年头啊,没有什么纯不纯的,只是他受到的诱惑还不够多。
周五的下午,好不容易结束了一星期的工作,现在健身房真的是没发呆了,一到夏天各式各样的妖怪都跑了出来,争奇斗艳的,健身房到处都充满着诱人的雄性荷尔蒙的味道,让人家的小心肝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我软绵绵的回到家里,心里痒痒的,到处都痒痒的,真想黄瓜在手,天下我有啊,我的张云已经好久没有和我那个了,我也没主动要求,女人啊,一定要矜持,要矜持。我懒懒的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把抱枕夹在双腿间用力的摩擦着,心里揣测着张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春药。张云回家了,好久没见他这么早回家了,总是借口忙忙忙,其实我是一个很好强的人,至少应该是江姐转世,其实我是不稀罕做女强人的,特别是像刘胡兰那种,因为不善表达,把“我舅是共产党”和“我就是共产党”混淆不清而丢了性命。我至少有刘胡兰的骨气,而且还具备她没有的机智和标准的发音。自从水母给我说了张云的事情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一直按兵不动,现在可能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我和张云之间应该马上会爆发一场腥风血雨的恶斗!
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风在哪里呢?张云换好衣服,走到沙发前坐了下来,用手臂环着我,我没动声色,继续看着电视。“老婆,我们又多久没有做爱了。”张云笑着问我。我没有回到,在一旁拌着手指计算,然后呆呆的说“我的手指不够用了,把你的手指接我用用。”张云没有欣赏我的可爱,然后淡淡的说:“老婆,你最近有点反常。”“我怎么反常了?”“我们一个多月没做爱,你都没有性需求呢?” 我操,没想到张云居然倒打一耙。“我怎么没有需求,是你自己不给啊。”“你都不要我怎么给啊。”“你不给我怎么要啊。”我们还是有心平气和的谈话开始升级到有点火药味的斗嘴了。“我怀疑你红杏出墙了。”张云冷冷的说了一句。“张云,说话可是要负责任的,这朗朗乾坤青天白日的,你凭什么说我出墙了?”我一下暴跳起来,妈的,张云已经触及到我了我底裤里的底线。你可以说我好吃懒做,可以说了面相丑陋,但是绝对不允许你说我不守妇道,作为一个女人,什么最可贵,贞洁!我圣神的贞洁!张云居然不问青红皂白的信口雌黄,我没有去解释,解释等于掩饰,掩饰等于编故事。
我在等张云继续批判我,我也在等待绝命的反击,他说得越多,就暴露得越多,总会找到他的漏洞一招致胜的。张云现在已经不是我的老公,而是战场上的对手,或者也可以成为史密斯父母,我们的乐趣就在于窝里斗。“没话可说了吧,你说你那么骚了,一个月不操你你受得了,你不痒了?”张云继续不依不饶的。我操,得寸进尺。“我是痒了,你呢?你一个月不射不把你的精囊给撑破了?说,你都和哪个小妖精滚混去了,别以为你在丰台那边的事情我不知道。”张云一下乱了阵脚,他显然不知道我会掌握他的行踪,女人啊,永远要给自己留一手。再此,我要感谢我妩媚妖冶的水母姨妈向我透露了张云在丰台的胡作非为,今天终于我成了转败为胜的重要砝码。“我在丰台的什么事情?你听谁说的。”张云眼里闪过一丝慌张。“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非常有姐姐的特务范儿。“我都做什么了,老子一直清清白白的,信不信一样把你操得哭天喊地的?”张云气急败坏的跳起来指这我骂着。吵架不是我喜欢的,但偏偏是我的强项,当0不可怕,就怕当0的有文化,想我可可饱读四书五经,满腹经纶,一直苦于没有用武之地,今天终于在张云面前派上了用场,我一定要和张云好好的吵上一架,最近一直心慌失眠潮热汗出的,以为是更年期到了,到现在才知道是性生活不协调,都是张云害得,想当年再怎么也是面带红晕有光泽,人送外号一朵梨花压海棠,朝阳东路小淫虫的我,居然被冷落的面容枯黄,靠黄瓜度日,真的是一入豪门深似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