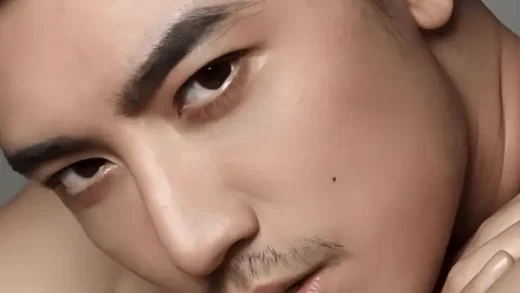“不管这些,你就说想不想我再回来。”
起初,老木没吱声,见我一直等着答案,他才用肯定地语气说:“想,当然想,咋不想呢?”
“真心话?”
“哥不说假话?”
“可你现在说的是假话!”我的声音提高了几分贝。
“咋是假话呢?”老木突然没了刚才的犹豫,一副破釜沉舟的样子,坚定不已地说,“想,哥想,哥是真想!”
“我不相信。”
“咋不信哩?”
“没有咋,就是不信!”
“要哥发誓?”
“没必要!”
“小元,咋了,生气了?”
“没有,我生你啥气,我没啥气可生的。”
“生了,指定生了,我看出来了。”
“看出啥了?”
“小元生气了。”
“是呀,我生气了,我生你气了。”
“怨哥,都怨哥,哥来晚了,让小元受委屈了。”
“不是的。”
“那是咋了?”
“我不想说。”
“说,告诉哥。”
“不想说。”
“小元,咋了?不相信哥了?”
“没法相信。”
“咋了?说给哥听听?”
“真要说?”
“说,哥想知道。”
“知道了又咋了?”
“哥不让小元受委屈。”
“不可能!”
“咋不可能?”
“你已经做了让我受委屈的事儿!”
“啥事?告诉哥!”老木似乎意识到我确实生他气了,而这个气他又不知道怎么来的,怎么就出在了他身上呢。
“说出来怕你生气?”
“不生气,哥不生气,哥不生小元的气!”
“当真?”
“当真!”
“老木,你记不记的你曾经说过‘一辈子对小元好’?”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天,马车上,老木举起了右手,表情严肃地说,我,乌山镇乌岭沟村村民陈丰,这一辈子,永远只和咱兄弟韩小元同志好!
此后,多少日来,我天天做梦,梦见他举起右手发誓说,这一辈子,只和咱兄弟韩小元同志好!
“恩,说过,哥说过,哥说过要一辈子对小元好。”
“老木说话不算数。”
“咋能?哥一向说话算话,哥指定对小元好,一辈子对小元好,哥说到做到。”老木抓起了我的手,把我的一只手放在了他的两只手掌中间,来回上下抚摩着,“你都不晓得,哥每天向李水军打听你的情况,一听说你病了,哥马上就赶过来。”
“老木,我晓得,我晓得你对小元好,可我想要老木一辈子对小元好,你也答应过要对一辈子对小元好。”
“恩,是,哥是答应要一辈子对小元好,莫非,你不相信哥能做到?”
我摇了摇头:“小元很希望相信你能做到,可小元无法相信。”
说着,我就拽着老木的手,呜呜地哭了起来。
本来我不想哭,忍了又忍,没忍住,我就哭了。
先是流泪,再是轻声地啜泣。啜泣着,我就想,反正也哭出声了,别说屋里,就是全校也找不到人影,我就索性大胆地,放声大哭了起来。
我这一大哭,把老木造懵了。
他抱着我,紧搂我的身子,脸贴着我的脸,安慰我:“小元,别哭啊,你要哥咋做才相信哥呢?”
哭声嘎然而止,我从他怀里挣脱出来。
我擦干眼泪,稳了稳气,恢复正常神态。我严肃认真地看着老木,用严肃认真地语气说:“老木,你说过要一辈子对小元好,是吧。”
老木点点头。
“你还说过小元该找个女人,娶个媳妇,成个家,是吧!”
老木又点点头。
“小元真要找个女人,娶了媳妇,成了家,你还咋一辈子对小元好呢,这不瞎扯吗?”
老木没想到我会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只是呆呆地看着,想说什么,动了动嘴,却没说出来。
我又接着说:“小元真要是找了女人,指定回城里结婚,真要回城结了婚,就会有孩子,真要是有了孩子,小元就舒舒服服过自己的小日子,小元真要舒舒服服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老木你上哪对小元好去……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谁都知道,我这是故意在抱怨老木;谁都知道,在这渴望已久的再次激情后,我的这些所谓抱怨,分明是藏着幸福的。
老木呆呆地听着。
“所以,老木,你说要一辈子对小元好,是假话,不折不扣的假话;你说小元该去找个女人,娶个媳妇,成个家,才是真话,埋藏在心的大真话。你无非是想,小元真要找了女人,就会离开这里,离开了这里,你老木就不需要一辈子对小元好,这样,你就不需要遵守诺言,也就不会背上违背诺言的黑锅……你是这样合计的,对吧,老木?”
老木仍是呆呆地听着,有点目瞪口呆了,脑袋晕晕的,没拐过弯了,好大一会儿,他才说:“小元,不是,不是,哥没那意思,没那意思,哥愿意一辈子对小元好……哥,哥是寻思,小元也不小了,到年龄了,该想女人了。小元要想女人了,就会去找女人,娶个媳妇,成个家……哥是寻思,小元这么年轻,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长得好看不说,还是大学生,城里的教书先生,条件多好,咋还能像哥,一辈子不找女人,不娶媳妇?”
“为什么不可以,老木可以小元也可以……小元就不找女人,不娶媳妇,一辈子不娶,我要老木对小元好,一辈子对小元好!”
我想也没多想,这些话语竹筒倒黄豆般,嘣嘣嘣,全倒了出来。
话都赶到这个份上了,本来,我想对老木坦白自己的性取向,想想,还是作罢。这事儿,不能太急,就这么说出来,他会转不过弯来的。
面对我突然近乎竭嘶底里的一连串抓狂话语,老木一下震住了。他死死盯着我,似乎是感动了,眼眶湿湿的。
老木说:“小元,你这么说,哥心里好生高兴,哥是说过小元该找个女人,娶个媳妇,成个家……咳,你都不知道,哥在家等小元电话,一直没等着……哥还寻思,这兄弟,怕是找着女人了,不稀搭理哥了……哥这心啊,好生不痛快。”
老木这么说,我心理似乎有了谱,我动了动身子,挣脱老木的怀抱,我说:“老木,我该起床了。”
老木一惊,揽住我的腰,忙问:“起床?小元,你起床干啥哩?”
“收拾包!”
“小元,你躺着,哥来!”
不等我回绝,老木快速穿衣套裤,脚下像装了弹簧,跳下床,故意把行李包的拉链狠狠拉了一下,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然后,不紧不慢,这碰碰,那蹭蹭——我心如明镜,老木是在用缓兵之计。
碰完这碰完那,老木开始往一个透明的瓶子里灌热水,灌完后,他递过来。
我抱着,好暖和。
我问:“哪来的瓶子?”
老木说:“医院挂滴流的药瓶,哥带回来了。”
老木问:“烫手吗?”
“不烫,温度正好!”
老木说:“我就怕太烫了,烫手,把开水倒出来冷了一会儿,又怕冷过了头。”
可能看到我脸上有说不出的感动,老木红着脸,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认识这么久了,他还是像刚认识那会一样,经常用这个动作来表示他的“不知所措”。
我说:“老木,回去吧,谢谢你照顾我,我也该走了,再不动身,回城车就过了。”
老木怔怔地问:“小元,真不和哥回去了?”语气带着哀惋。
“不了,小元要回家,要回家找女人、娶媳妇、成家了。”
“那,小元不要哥……”老木语气一层层暗淡下来,就像一艘逐渐下沉的船,后面的话不仅我没听见,估计他自己也听不见。
“是你不要小元了。”
“哥咋能不要小元呢?”
“老木,你回去吧,家里没人,猪都会饿死。”
“猪杀了。”
“狗呢,我送你那条小黄狗呢?”
“皮皮喜欢着呢,天天领着它玩!”
“牛呢?得天天牵去外面吃草。”
“我交代英子了。”
“她会把你的红衣服偷走。”
“她找不到,我藏起来了。”
“你就送她呗,她那么想要,反正也没有别的女人可送。”
“她是锁子媳妇!”
“那,送……”后面的话没完,我就又吞了下去,我感觉好象又已经走到了一个危险的旋涡附近,再说,就又要一头栽了进去。
老木却走了过来,静静地坐在床沿,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
我突然有些害羞,赶紧闭上眼。
也许是我闭眼的样子让他着迷,老木把手在裤子上使劲蹭了又蹭,然后用右手轻轻地抚摩我光洁的脸蛋和额头。摸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手真是太粗糙了,他甚至因为疼惜我而变得于心不忍。
老木一遍又一遍轻轻抚摩我的脸,并不停轻轻捏着我鼻子,又松开,再捏紧,再松开。重复这个动作使他感到非常愉快。他甚至想起自己很小的时候跟邻居的丫头在一起玩,那时他经常用手捏她们的鼻子。
捏完,老木的嘴巴甜得像哈密瓜,老木说:“小元,你的脸蛋真细腻,真光滑,像小姑娘的脸!”
我说:“喜欢吗?”
“喜欢。”
“我也喜欢老木的脸。”
“小元。”
“恩!”
“跟哥回去不?”
我没说话。
“跟哥回去,啊,住几天,哥给小元熬点中药,补补身子!”
我还是没说话,却睁开眼,笑眯眯打量着老木,极像只饱食后躺在草坪上慵懒打着滚儿的食草动物——餍足而无所事事地回味。
老木又说:“不行,小元,你还没好利索,得跟哥回去。”
我这才不紧不慢地说:“小元倒是愿意跟你回去,但小元身子骨很好,不需要补,再说,就算要补,小元可以回家补……你要实在希望小元跟你回去,你就找出一个说服我跟你回去的理由来。”
老木想了想,说:“行,小元,你等着,哥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
我说:“老木,你上哪去?”
老木说:“小元,你先睡一觉,醒来就知道了。”
说着,老木出了宿舍。
咚咚咚,脚步声由近渐远,直至消失在空旷的走廊。
第二十一章
许是累了,许是这段时间一直绷着的心,松弛了下来。
很快,我就感到了阵阵困意。
抱着暖暖的水瓶,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醒来,已是下午。
我叫了声老木,没有回应。
穿衣起身,打开宿舍门,校园一片空旷,冷清得一个人影也没有,漫无边际的寂静,像一张无边无际的宽大网笼罩校园。
我在寂静的校园里跑着,不停喊着老木。悲凉的回音,在冷冷的薄雾里荡漾开来。
远处,几株树,似乎在寒冬冷空气的袭击下,瘦长且不带旁枝地立着,寒风一吹,零零落落,左右颤抖,有着一股萧杀的悲凉和沧桑。
这一刻,我的脑子是明明灭灭的,恍惚着,偶而,寒风吹来,我猛然一颤,我就嘿嘿地笑了,自言自语说: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嘿嘿!狗屁!什么都不是了!嘿嘿……
突然,我就觉得,时间就像是有起点而无终点一样,某种激烈的情绪向着未来扩散开去,最后被广大的虚无吸收了,或者它沉淀下来,在我的身体里逐渐地聚集、凝结,形成了一个不易察觉但时感刺痛的点。
我扛起行李就往镇上奔。
晚了,
一切,
都晚了!
回城车一天只有两趟,上午一趟,八点;下午一趟,一点。
呼啸的北风,说来就来,那样的大,那样的响,像小兽在屋前屋后呜呜地哭,小孩个个冻得挂起了清鼻涕,拢着两只袖口贴着墙根慢慢地走。
车站的门口,我并未离去,顺着车站,来回跺脚——我希望有奇迹发生,搭上回城的顺路车。
左侧的小饭馆飘着浓浓的大骨头香,老板娘说:“刚熬的新鲜肉汤,要不来点?”
我摇摇头。
虽然,好几天没怎么认真吃东西了,可我还是不觉着饿。
右侧,有个男孩静静地站着,站了一会儿,学我,来回走动,不停跺着脚。许是同样的境遇,他跺着跺着,就靠了过来。
男孩问:“哥,你也等人?”
“嗯!”我嘴角动了动,本不想回答,还是出了声。
“等女朋友吧!”
我看着对面的山,没再吱声,勉强地笑了笑。
“这么大的风,还在等呀?”
我还是没吱声,勉强地,微微一笑。
外面,确实很冷,风确实大,吹在身上,针刺般痛。
“唉,我也等女朋友,她上同学家玩去了,说好今天回来,这么冷,风还大,我给她带了衣服和挡风伞”他继续说着。
我看了看他,一脸的焦急,手里一直拎着装衣服和伞的兜儿。
突然,远方来了一个女孩,他急急地说了句:“哥,我先走了,我女朋友来了。”说着,他就急匆匆跑了过去,女孩飞奔而来,和他抱在了一起。
他们手牵着手,背影渐行渐远,消失了。
男孩走后,我坚持了一会儿,背起包,凄凄然,离开了。
镇街道,赶集的人群潮水般散去,只剩下三三两两不怕冷的,披着露出白白棉絮的外套,在游离晃荡。
镇礼堂,苍穹屋檐下,几个农民穿着班驳的粗布衣服,围圈扎堆,在甩着扑克牌,粗犷地说着话。
旁边,一位“算命先生”,卦摊摆在旁边,地上放一张纸,上面写着:“为你的情感当参谋”、“帮你的事业、升学指出阳关道”。
这里算命先生很多。
夏天,每逢赶集日,他们顷巢而动,从四面八方赶来,在乌山大桥一蹲,冬天则云集苍穹礼堂一角,眼睛在来来往往行走的人群中飘来飘去。
我向来不信周易八卦,掐掐算算之类的东西。
那些个算命先生,就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游离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那些目光呆滞、表情木然或痛苦或悲愤或惆怅的人。不知有多少人在他的卦摊前痛哭流涕,诉说着爱情上的失意、生活上的烦恼、人生旅程上的坎坷。
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
初来乌山镇,也有算命先生跑过来冲我说“先生,要算命吗?我能窥知你婚姻的奥秘!”我理也没理,掉头就走。
这一次,我没走。
不得不承认,这位算命先生有一双鹰隼般的眼睛,他一下就看出了我目光中的焦灼与烦躁。
当他冲我说了一句“先生,瞅面相,你命犯桃花……”时,我想也未想,蹲了下来。
算命先生老谋深算地问:“先生,看什么?感情?”
我说:“是的,看感情!”
我说我身边有两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和他们的感情。
当然,我没说这两个人是男是女,我只想知道,这所谓的算命先生,究竟怎样来为一个喜欢男人的男人的感情做参谋。
算命先生说:你先想着那两个人。
我说,要不要分别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
算命先生说:不需要,你只要在心里想着他们就行。
我开始想象着康兵的模样。
过了一会儿,算命先生说:好了,下一个!
我又开始想象老木的模样。
没过多久,算命先生拿起笔在纸上写着。
写完,算命先生说,这是你和那两个人的感情信息。
我接过一看,正面,他写了三组数字:11,8,11。反面,他同样写了三组数字:8,11,8。
算命先生说,正面是你和第一个人的信息,前面的11,表示你们之间一直平行交往,没有交叉。中间的8,表示你们两个平行交往了一段时间后,互相靠近,交汇,纠缠在一起,完后,又相互远去,最终,又成了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我一惊!
算命先生接着说,反面是你和第二个人的信息,8字,表示你们像拧麻花似的,纠结在一起一段后,分开了,成了11,两条互不搭理的平行线。但你和她(他)之间,注定是拧麻花关系,很快,你们又成了8,又像拧麻花似的,纠缠在一起。
我又是一惊!扔下钱,把那张纸片塞进裤兜里,逃之夭夭了。
有时候,不得不佩服那些算命先生,他们并不求数量给人门庭若市的效应,追求的是猛虎出更一扑致命的境界。
看看这位算命先生就知道了。
41
第二天,我醒得早。
我一直没怎么睡着,脑袋全是老木的影子在晃来晃去。
我对自己说,不要再想了,忘了吧,把他忘了吧。
但,我无法控制,我在想,我爱老木,爱得如此卑微,像追逐太阳的向日葵。我还在想,老木内心,并不爱男人,却也不拒绝我对他的好及诱惑——这是最让人暗然神伤的了。
想着想着,头就痛得厉害,痛着痛着,天,亮了!
起来,我扛着背包,我决定改乘早八点大巴回城。
外面,刮了一清晨的风,突然停了。
我深一脚浅一脚,跋涉在冰与土混淆的通往镇上的泥路里,蹒跚在漫天雪雾中。
镇车站的大马路上,我一直远眺着。我看了看远处的旷野,要过年了,小镇这几天,天天是集市,三三两两赶集的人,挑着担,挎着篮,从四面八方赶来。
回城大巴来时,太阳从破棉絮似的云堆里钻了出来,给枯黄的山峦抹上了一片金黄。
我心里想着
别了,乌山镇;
别了,康兵;
别了,乌岭沟村;
别了,老木!
大巴车停住,上车的人鱼贯而入。
我刚要上车,就听得后面传来急急的喊声:“师傅,等等!”
声音很熟,每一个字不是吐的,而是被浑厚的舌头挤压成扁扁的一团,化在气流中磕磕碰碰地滚出来。紧接着,一个影子旋风般飘了过来,从后面一把揽住了我,没等我反映过来,影子说:“小元,先别上车,哥有话说。”
回头,是老木。
眉毛头发都是水珠,脸上额上涔着细细密密的水滴,也不知道是汗水还是雾珠,抖一下便噼里啪啦往下掉。
“老木,是你?……车要走了,我得上去……”看见老木,我一直控制得很好的脸部表情骤然被打乱了,脊背上的肌肉突然发紧,我赶紧做出要上车的姿势,以掩藏起自己复杂的心情。
“小元,别上车,哥有话对你说。”老木露出无措的表情,还有他的眼神,突地躲闪、慌乱起来。
司机等得不耐烦了,冲我们喊着“还走不走了?”
老木冲司机摇摇头,正襟危坐地说:“不走了,不走了!”
“有病!”司机骂了句,踩了一下油门,大巴车一溜烟,跑了。
大马路上,老木紧紧拽着我,我奋力挣扎着,我冲着远去的大巴车说:“别拦我,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爷爷奶奶。”
老木却不撒手,死死抱着我,
我挣扎得更厉害了。
老木的力气真大啊,挣扎着,我就像一只困兽,困在了一堆泥淖中,无法动弹。
见我安静下来,老木说:“小元,哥来接你回去。”
“我没说过要跟你回去。”
“中药都准备好了,就等给小元熬。”
“我没说要喝什么中药。”
“老中医说了,喝三天就见效,早一副晚一副。”
“要喝你自己喝!”
“还有人参,哥从柜子里找出来了,老好了,样儿一点没变,和刚挖的一个样。”
“不要,不要,我不要,我要回家。”气不过来的我,大声嚷嚷着,每个字语调都是上扬的,尾音颤颤悠悠。
嚷着嚷着,我就对准老木的脖子狠狠咬了下去,死死咬住,不放。
老木身子陡然一颤,很快恢复原样,保持静止不动的姿势,任由我咬着。老木死死地抱着我,像水绕岸一样绕着我,任我怎么踢、撕、咬、捶,作困兽状地变换形状,他都柔顺应和。
很快,我就放弃了徒劳的挣扎和泼赖,安静下来,两个人粗重的呼吸声像两股巨风从不同的方向刮来刮去。
也不知这两股风刮了多久,我终于挺不住了,我说:“老木,放开我!”
老木见我不再挣扎,安静了下来,他松开了紧抱着我的双手。
我说:“为什么要拦着我!”
老木说:“小元,跟哥回去。”
“我不想跟你回去。”
“我给你……”
“不要,我不要,我不喝什么中药。”我又有点气不打一处出。
“我给……”
“我也不喝什么人参炖鸡肉。”
“我……”
“我都说不要了……!!!”
还没嚷完,我就看见眼前一片红亮亮的东西在晃呀晃。这东西可真红,红得像一团火,一团发着光、发着热的火,晃得我目眩,烧得我头晕。
老木说:“小元,哥送你的,拿着!”
“什么呀?”
“红衣服!”
“啥红衣服……?”
突然,我就哑住了,咬着舌尖,脑袋空白着,竟找不出其他别的话来说。
第二十二章
宿舍里,老木从黑布袋里掏出肉酱、虾酱、咸鱼、花生米和洗干净的蔬菜,整整一大包——如果说,老木的突然消失让我感到吃惊,那他突然又拿着红衣服出现在我跟前,只能让用离奇来形容,我感觉自己,在经历着一种似乎只有电影里才有的离奇剧情。
我说:“老木,你坐!”
老木停止了手中的动作,乖乖坐在了床沿,像一朵莲花,毛细血管从皮下透出,小蚯蚓般娇憨地弯来弯去。
我说:“老木,红衣服送我了?”
“恩!”
“真送?”
“真送!”
“为什么要送我?”
老木却不说话,神情像一只等候发落的羔羊。
“老木,你不说出理由,小元不能要。”
见我神情如此严肃,老木又有点正襟危坐,一双宽板大手绞来拧去,一时不知咋办才好。过了好大一会儿,他才嗫嚅着说:
“你那天向哥要,没给,哥估摸小元生气了。”
“生啥气哦,都过去的事儿了!”
“小元生气了!”老木似乎受到了鼓励。
“没有!”我在狡辩。
“指定生气了!”老木如此的肯定。
“你说生气了就生气了?”
“哥有证据。”
“啥证据?”
“小元一直不给哥来电话。”
“这就是证据?”
“小元还给自己买衣服了!”
“我给自己买了衣服?”
“恩!”
“啥衣服?”
“红衣服!”
“胡说,我没买,我买那玩意儿干啥,女人用的东西!”我像突然被切中要害,激烈地辩解着。
“买了。”
“没买。”
“哥看见了。”
“看见了?”
“看见了。”
“哪呢?”
“枕头底下。”
“哎,你说那件呀,那是我给别人带的!”我有气无力作着最后的辩解。
傻子都知道,我在撒谎。
我确实买了件红衣服。参加完康兵婚礼,返校,路过镇大街,有家服装店新开张,老板吆喝着“服装哩,刚上货的各款新年服装哩!”
无意一瞥,店内雪白的墙壁上,挂着一件红得像火的衣服。进店,竟和老木压箱底那件相似。鬼使神差,我掏出钱,买了下来。
回校,天突然下起了雨,还飘着雪,我把红衣服举在头顶,飞快地跑,风很大,红衣服飘啊飘,像新娘的红盖头。
我拼命跑,红衣服不停飘。
我跑着跑着,
哭了!
回到学校,
病了!
“小元!”
老木靠了过来,把红衣服塞到我手里,“哥说过要一辈子对你好!”
“老木……”我两颊绯红,神情羞涩,眼睛里渐渐地涌出了泪水,再也忍不住,抱住了老木,抱着,泪水像决了堤的河流淌到脸颊。
我伸手摸了摸他脖子上被我咬红的唇印,心疼地问:“痛吗?”
“没事,哥粗皮糙肉!”
“真不痛?”
“不痛,就是痛,小元咬得,哥也得忍!”
扑哧,我破涕为笑,笑的时候,脸上的两道泪痕裂开了。
见我笑了,老木脑袋一歪,看着我,也笑了。
我把脸埋在老木颈脖,轻轻亲了一下我留下的痕迹,脸上的泪水也弄湿了他的脸庞——真后悔对老木下了这么狠的“嘴”,他可是我喜欢的人呀!
床上,我和老木紧紧搂抱着,相互注视着对方。
突然间,我感觉老木变了。他注视我时的那种一往情深的眼神让我感动,我甚至产生了在他的注视下死去的冲动,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和老木在一起,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永远的永远!
投稿请发往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