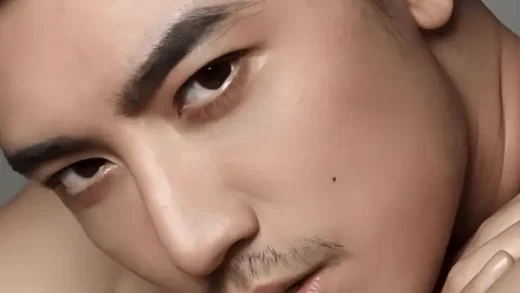再说了,这孩子自第一天和我照上面,就比较亲,下课了还特意跑过来说“老师,你讲得真好”。后来,生病了,拿自己采的中草药来看我。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啊,我很是感动。
我说:“恩,老木,我相信你,你也是我见过的,天底下最好、最善良的农民。”
老木脸突地一红,憨憨地笑了。笑完,老木再次问:“小元,康大宝那边,真没事?”
我露出了灿烂的笑,我笑着说:“没事,怎么会有事呢?元旦我还要上你家吃新鲜猪肉呢!”
老木爽朗一笑,说:“好咧,哥在家等着你!”
第七章
返校后,本来,我想直接找康兵,责问他为啥这么卑鄙。
但,我忍住了。
我是感觉到了康兵的变化的。
自那次意外冲动事件发生后,康兵的脸,像是六月的天,安了根灯绳,拉一下,风高夜黑,再拉一下,阳光灿烂。一会儿圆,一会儿缺,还没等你把“月光明媚”瞅个仔细,它却早已躲在云朵后“月朦胧鸟朦胧”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和康兵在一起,我感觉他像个孕妇,敏感、多疑,弄得我战战兢兢的,动作大了,怕流产,动作小了,又怕将来难产,折磨死人了!
第二天上课,我是带着一股火走进课堂的。
进了教室,我看到教室后排多了一张椅子,猜想可能是有某个老师来听课。等上课时,发现那个听课的人竟是康兵!
他穿了一件米黄色的高领夹克,样子很像我送老木那件,但我知道,不是。
虽然,他剪了个小碎头,整个人显得格外清爽,可我突然就觉得他的样子简直丑陋之极。
那堂课我上得很用心,讲的义愤填膺、激情滂湃,我双手一直学着他,不停做着夸张的飞舞动作。
我给我的学生讲人活着的意义,我还特意讲了臧克家的《有的人》这首诗——: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有的人,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有的人,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有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有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我把这首写在黑板上,字体大大,方正、遒劲。
我说,以前我在城市里忙碌,很少想过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到了这里,尤其是看到从小煤窑里爬出来的赵小良,我开始认真地想了,而且想得很多。
我问学生:生命的意义有没有层次?
学生瞪大着眼睛,不知所措看着我。
我又故意问康兵,我说,康老师,你认为生命的意义有没有层次呢?
我的问话显然让他感到有些局促,他挪动了一下身体,椅子发出轻微的“咯吱”声。
我很得意于他的反映,我像自己给自己答案似的说,当然是有层次的,就拿这一带的大煤窑主和赵小良的父亲来说,就完全是两个层次上的生命个体,大煤窑主的手下把赵小良的母亲拐跑了,赵小良的父亲却还要去煤窑给他背煤。
愤怒中,我看不清康兵的表情,看到的是自己的嘴,在不停地上下来回,动来动去。
突然,他近乎哀求似的说,韩老师,你不要说了!
接着,他眼眶带泪冲出了教室。
看着康兵冲出教室的背影,我似乎从空气中闻到他泪水的味道。
走出教室,起风了,天边有一大朵铅灰色的云彩,看着像要有一场大雨。
天气开始冷了,教室里的窗玻璃经过一夏天,变得残缺不全,冰冷的风吹进来,孩子们上课时都在打哆嗦。学校还没换玻璃,最后只能用厚厚的塑料膜把窗户糊上。
自从那次听课事件后,我和康兵的关系像翻了脸的门神,彻底不相往来,连话都不说了,完全像两个陌生人一样。
直至一天,赵胡子(赵小良父亲)领着赵小良过来。看见我,赵小良兴奋地说:“韩老师,我爸爸回来了,我又可以上学了!”
我似乎料到了这样的结局,摸了摸赵小良的脑袋,我说:“进去吧,马上要上课了。”
赵胡子掏出一叠钱,说:“韩老师,谢谢你,这钱还你。”
我连忙摆摆手:“留着吧,给老人看病用。”
他摇了摇头,神情立马悲伤起来,他说:“韩老师,用不着了……是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没及时治疗。”
说着,他的眼泪就流了出来。
我听了,心一紧,立刻浮现出那个骨瘦如柴的老人,有气无力的咳嗽,每咳嗽一下,似乎都要用尽全身的力。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我说:“你回去吧,小良的学费不用担心,我帮他缴。”
他脸上露出了一丝笑,顿了顿,他说:“韩老师,我把小良的学费交了,还把媳妇找回来了。”
在我的追问下,他才告诉我,学费是康老师帮他交的,他的媳妇也是康兵的父亲康大宝帮忙找回来的。还说,康老师嘱咐他,千万别让别人知道,尤其不要让韩老师知道。
此后的几天,心中的那股火,慢慢下去了,那次讲课时的冲动早已淡然。
一次课间,看见康兵,我鼓起勇气过去,我问他:“康老师,能去听你一次课吗?”不管怎样,那是很早就和他做的约定。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听课时,我特意穿了一套西服,那是我在城里听课时养成的习惯。
那堂课,他上得很用心。下课了,学生们四散而去。我在走廊里等他出来,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迎着我的目光走过来。
他问:“韩老师,你怎么想起来听我的课?”
我说:“我答应过要听你的课!”顿了顿,我又说:“康老师,你的课讲得真好!”我这话说得很诚恳。
他没吭声,过一会,他才问:“韩老师,你怎么不来吃饭了?”我说,总是麻烦你,我不好意思。他“咦”了一声说,麻烦啥,只是多一双筷子,你吃方便面要吃出病的。
他的话让我终于绷不住了,轻声笑起来。
见状,他说,晚上过来吃饭吧,我给你做蘑菇炖小鸡。那是他的拿手菜,我想都没想便点点头。
宿舍突然停电,吃过饭,我和康兵就坐在昏暗的房间里,风从门缝间钻进来,房间里冷得像冰窖一样。他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黑暗中模糊成很小的一团。
见气氛有些尴尬,我找话题说,在城市里这样的天气早该有暖气了。他问:“你家的暖气暖和吗?”
我说:“是啊,地热。”
他说:“地热?那可真好,多舒服啊!”
我看不清他的脸,但能感觉到他脸上灿烂的微笑,带着暖意。
我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元旦的假期上,他小心谨慎地问:“元旦有什么打算吗?”
我随口就说:“去老木家。”末了,我说:“咦,不如你跟我去好了,老木元旦杀猪,可肥了,三百多斤哩……”
我的话还没说完,我就看见他脸色一变,身体的某个部位犹如针尖划过,微微一颤。良久,他稳了稳神,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试探性问:“韩老师,你能不去吗?”
我似乎读懂了他眼睛里包含的渴望内容。
我想了想,说:“不行,和老木早约好了!”
他脑袋微微一垂,脸色暗淡下来,没再说什么了。
元旦前一天,我接到了老木的电话。
老木说:“小元,来啊,一定要来啊,哥在家等着你呢。”
听见老木的声音,我很兴奋,我仿佛看见了他在村委会阴冷的小屋,一边跺脚、呵气,一边摇头晃脑给我打电话。我还想起了那首歌儿: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尝尝家乡菜,团圆乐开怀……
晚上,我在宿舍打着包。
我决定送老木一床新弹的被子,加厚的,九斤重。
在下第一场雪之前,我找了镇上的一个棉花匠,为自己弹了一床厚厚的棉被,学校宿舍太冷,没有暖气,而我不大会生炉火,总把学校发的炉子弄得一团糟。
那个弹棉花的老师傅很厉害,微微弯曲的身影在小屋漂移,弹锤起落,奏响的音乐韵律合着空荡房屋里的回声,此起彼伏。和声里,洁白的花絮欢腾着,随风飘舞。
我不知道保尔;瓦莱里所说的“一种令人心平气和的、幽静的神往”是不是表述的这般境界。
但,我是醉了!
我醉了的同时想起了老木,我在老木家住过一次,被狗咬伤那晚,睡大炕。老木家只有两间房,在厨房的一左一右,左边是仓储室,没有炕,堆满了凳子、椅子等物品,还有个地窖,地窖存放着地瓜、土豆、萝卜之类的东西。右边才是睡觉的炕房,大炕的一头连着厨房的灶堂。
睡觉前,老木把铺的褥子,盖的被子拿出来。都是又小又窄的单人褥和单人被。老木先把我要用的褥子和被子铺好,再把自己的铺好。
老木说:“先生,可以睡了!”我钻进了被窝,他也钻进了被窝。两个被窝虽说挨得近,却是独立的个体。由于被褥太薄,山里风大、天气凉,半夜,我冻醒了,接着,受风寒了。
而在赵小良家住那天,我一直拽着老木的手。起初,睡不着,看着老木的脸在月色下,黝俊、迷人,尤其是那下巴的那道疤痕,像个小精灵,在我心里跳呀跳,我很想伸手去摸,但我不敢,我实在找不到借口,我总不能不顾一切钻进他的被窝,抱着老木说:来,老木,让我摸摸你的脸。毕竟不是女人。何况,左边还有赵小良,十四岁的男孩,什么都懂了。
我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就决定送老木一床又厚又软的双人被。弹棉花的老师傅说:“小伙子,你要结婚了吧!”
我一楞,脸色微红。
老师傅接着说:“你算是找对人了,抱着新媳妇盖着我弹的新棉被度春宵,那个舒服哟,保你一辈子忘不了!”
我的脸更红了。
那一刻,我想到了老木,想到他家又小又窄的单人被。我幻想着自己和老木挤在一个被窝,盖着我送他的双人大被,他搂着我,用下巴性感的胡子扎我的脸,扎得我痒痒的。
这么想着,我的脸红得燥热起来。我对老师傅说:“你再给我弹一床吧,用最好的棉花,比那床还要大、要宽、要厚实!”
说完,我知道,对老木,我的心,已经动了。这心,要是动起来了,就不是自己的了,做事情就不受控制了。
是的,之后对老木做的很多事情,就是从动一下心开始的,如果不想让一些事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自己心动。只是,有的人,比如说我,还比如说康兵,不让自己心动,却不能真的可以做到。到了某一时刻,就把心动变成了行动。
为棉被打着包时,走廊里传来吉他的声音,探头,透过玻璃窗,发现是康兵在弹着吉他,边弹边唱:
忘了吧,曾有过的瞬间幸福
算了吧,一切已结束
我知道他不属于我,我的心却被带走了
天空飘着冰雪,无法冻结我的思念
你的爱到底给了谁,我的心为你流着泪
所有的痛留给伤悲,象你曾经这样
(爱不爱我,告诉我有没有爱)
你的爱到底给了谁,我的心为你流着泪
谁能做到不顾一切,象我这样爱着你
这是零点的歌儿《你的爱给了谁》,淡淡的忧伤,和着这旋律在走廊里弥漫开来。
那晚,康兵变化很大,不仅弹吉他、唱歌,连思维也变得混乱了起来,成了一个言行怪异的男人。他弹着吉他,弹着弹着,就把吉他一扔,跑去了操场,围着操场,迎着雪,转圈儿跑,边跑边仰头大喊:让暴风雪来得更猛烈些吧!
敲钟的刘老师说:“这孩子,八成是又犯病了,去年这时候,也犯这毛病!”
一个教初三语文的老师告诉我说,康兵是个言行怪异的人。他还说言行怪异的男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神经质的男人。他说神经质的男人是正常男人中种类最可怕的一种,也是大家最不愿接近的男人,稍不留神,就会向神经病方向转化,变成非正常男人。
投稿请发往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