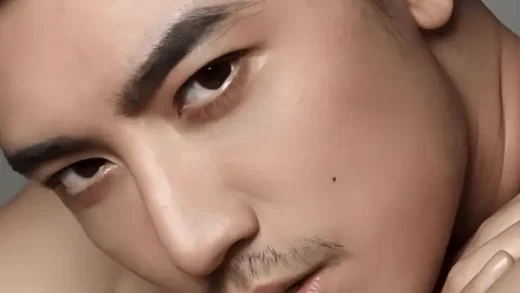他扔下烟头,就窜了过去。
跑出来的兔子没有地方跑,只能顺着兔子道朝林子中间跑。尽管跑到了林子中间,却不是每一个兔子都会撞上兔子套的,就算撞上了,也不一定会正好能套住兔子的头。这只兔子就相当狡猾,只见它灵活的身体在碰到铁丝的一刹那,倏地闪到了一边,躲过兔子套。
“哎呀,太可惜了!”我惊叹道。话音刚落,又一只兔子出来了,个头明显比前一只要小一号。
它顺着兔子道朝林子中间跑时,许是没经验,一头钻进了兔子套。套住的兔子不甘心被套住了,蹦跳着想逃走,却没想这一挣扎晃动了树枝,让站在林子边的老木知道有兔子被套住了。
老木提着一根棍子快速跳过去,朝套中的兔子使劲打下去,却没打中,兔子蹦一下,又突然逃走了。可顺着兔子道往林子窜时,窜错道儿了,刚好与黄狗相遇,黄狗跃过积雪,一下把野兔扑倒在地。
黄狗叼着四腿一蹬蹬的野兔来到老木跟前时,我从北边赶过来,都看傻了,冲老木说:你真行,还真管用啊!
老木说,不是我行,是你行!要不你一直在那又喊又敲的,把兔子赶到了套子里,别说狗,就是神仙也逮不着。
此后,我更来劲了,像个疯子,又敲又喊又叫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几个在灌木丛里敲打了半天,就是不见再有兔子跑出来。
敲到后来,我也泄气了。
老木安慰我说,小时侯,他经常用这种方式去逮野兔,每次都能拎好几只又肥又大的野兔回来。现在不行了,林子少了、灌木丛少了、草也少了。有时跑去林子里转半天,也看不见野兔的影子。
不管怎么说,总算还是逮着一只。
我们拎着野兔往家赶,地上是厚厚的雪,天上是一个大大的太阳,阳光照进雪里,雪的白里还透着蓝。
一阵风吹来,把树枝上残留的雪刮落下来,掉在了前面的锁子的颈脖上。锁子冷的发颤,不停摇着脖子,我们哈哈大笑起来。锁子不明白事理,以为我和老木偷袭了他。他低头抓起一把雪就朝我和老木扔了过来。
拍!雪球砸在了我的身上。我不甘示弱,把野兔往雪地一扔,捧起一大把雪朝锁子拨去。
刚刚赶兔子懒散的锁子,这会儿倒是勇猛起来,抓起雪团追得我到处跑。我边跑边向锁子还击,只是力气有点小,总是不能砸到锁子的身上和脸上。却让锁子的雪团在自己的头上开了花。还有雪团的碎块顺着脖子掉进去,在胸前化成水好像把内衣弄得有点湿了。
不过,这并没有让我有一点的不开心。因为,我看见老木笑了,笑了的老木也加入了进来,他时而把雪团扔向锁子,时而扔向我。扔向锁子的时候,老木喊着:锁子,看你往哪儿跑?从小到大你就没赢过我。锁子不甘示弱,奋力反击:现在我就赢你,现在我就赢你!
老木和锁子在半山坡上互追着打雪仗,一件看起来不可能发生的事,一下子发生了,不管是谁心里都会高兴的。
这不仅让我身体里有了过去没有的感觉,好像一部分不安的骨头变得酥软了起来。这甚至也感染了皮皮。
一旁观看的皮皮也笑了,皮皮笑出了声。笑声很好听,脆脆的,像是有一群鸟在飞。
又一阵风吹来,卷枝桠上的残雪,飘在空中,纷纷扬扬。
皮皮突然喊了声:看,大鸟!
我、老木,还有锁子,停止了追逐,皆抬头仰望。果然,天空中飞翔着一只黑色的大鸟,时而向上,时而向下,威武壮观。
蓝天,白云,黑色大鸟,雪白的山野、树林和土坡,多美的一副画啊。我叫了起来:哇,好大一只鸟,是雄鹰吧。
锁子说:我看是鹰,老鹰!
皮皮问老木:大爷,是老鹰吗?
老木不说话,盯着黑色的大鸟,和我们一起欢呼,喊着:快,快,往这儿飞!直至黑色的大鸟果真朝我们飞来,越来越近,正盘旋着向我们飘来,我们这才看清,既不是黑色的大鸟,也不是什么雄鹰,而是一只黑色塑料袋的碎片。
蓝天白云,雄鹰展翅,我还以为是只雄鹰呢!
哈哈,我们哄堂大笑起来。
回家的路上,我和锁子还在讨论那只雄鹰。我说怎么看起来那么像,锁子说是啊是很像。是啊,日常生活中,人的内心能轻而易举地幻化出许多奇妙的东西,或美或丑。它们逼真得近在眼前,与我们的内心感受遥相呼应,而全然不顾事实的真相。
我问老木:“你是不是知道那不是一只鸟?”
起初,老木没回答。等下了山,到了大马路上,老木才问锁子:“你知道为什么来这个山林逮野兔吗?”
锁子说:“还能为什么?这个山林你熟贝!”
老木摇摇头,老木说:“这座山林的北面有一块咱村比较聚集的墓地,逢年过节,村民都会用塑料袋装一些吃的祭租扫墓,野兔就喜欢在靠着墓地的这个山林扎窝。”
我说:“老木,原来你真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是个塑料袋啊,怎么不早说呢?害我们白高兴一场。”
老木说:是啊,我知道,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没说出来,是看见你这么高兴,不想扫你的兴,恩,还有,我也想让你们多高兴一会儿!”
这个老木,哈哈,我们又是大笑。
笑完后,我看着老木。阳光照射下的老木,是那么恬淡。我突然有种感动。其实,客观世界对于大多数人都是差不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人也是差不多的,但人们的感受却不一样。生活到底是怎样的,是美是丑,有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心中的种种幻化和自我产物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把天空中扫墓装食品用的黑色塑料袋看成是雄鹰,也可以把真正的雄鹰看成是塑料袋,美也好,丑也好,有时全是我们是何种心情,保持良好心态,往往比客观世界本身更重要,就像老木,他明明知道那就只一只黑色的塑料袋,但他却没有点破,把他当作雄鹰,和我们一起欢呼。
这次打猎,虽然只收获一只野兔,可你觉得这次打猎,收获的不光是只兔子,还收获了美好的亲情和美好的心情。看着老木和锁子互相追逐着打雪仗,我觉得阳光都照进了我的骨子。
玩够了,回家,老木把野兔子吊在门柱子上,拿出刀子,三下两下,就把兔子皮剥了下来。
老木把剥了皮的兔子分成两份,一份给锁子,一份自己留着。老木把自己的那份又切了一半,用刀子切成了块儿,洗干净了,放在盆子里。里边放了盐和辣子面儿,拌匀了。又用刀子,削出了很尖的小棍子。一下子削了有十几根。把切成块儿的兔子肉串在木棍上后——当然,这些都是老木背着我,偷偷做的。
我和老木吃过一次烛光晚餐。这是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事情之一,我连着感叹了两句:哇,烛光晚餐!
烛光晚餐是因为停电,说是下大雪,哪个山头的电线绷了。
晚饭很简单,吃饭时,皮皮也和我们一起吃。皮皮是陪她妈英子去小卖店买蜡烛,路过老木家门口,溜了进来。
许是没请我吃饭,英子觉得不好意思,不让皮皮进来,英子说,儿子,别进去,大爷家来客人了。我听见了,从屋里出来,我从口袋里拿出盒巧克力在皮皮眼前晃了晃,我说,皮皮,看,这是什么?皮皮问:是什么?我说,你进来呀,进来就知道了。皮皮挣脱英子的手,跑了过来。我把巧克力递给皮皮。皮皮说,这是什么啊?我说,这个东西可好了,城里的小孩都爱吃。皮皮说,真的吗?我说,城里的孩子为啥长得白,长得好看,长得聪明,就是因为爱吃这个东西。英子听见了,接过话:那咱皮皮可得吃!皮皮像是接到命令,马上打开了,拿出一块放到嘴里。英子问:好不好吃?皮皮皱了皱眉头:不好吃,有点苦。
皮皮跑出铁门,把剩下的巧克力往英子怀里一扔,再溜进老木的里屋,说:看还有啥别的好吃的!由于天黑,里屋暗,火还不亮,皮皮在几个熟悉的点好一阵翻找,却一无所获。
皮皮说:大爷,你把奶糖搁哪了?
老木端着热气腾腾的兔肉汤进来:吃啥奶糖,吃饭,啊,大爷给你炖野兔肉了。
皮皮不乐意地撅了撅嘴,爬上了桌,不情愿地夹了根芋头条,放进嘴里吃了起来。
老木问他:好吃吗?
皮皮皱了一下眉头,没说话。估计是因停电,芋头没烀熟,有点夹生。
我连忙也夹了一块,还不等咀嚼,我就连忙说,恩,好吃,真好吃。我一边吃一边作出一副很好吃很满足的表情。老木不放心,以为我是敷衍,但看到我无比认真还满足的样子,裂开嘴,放心地笑了。
晚餐进行到一半时,皮皮突然就笑了起来,先是扑哧一声冷不丁的笑,随后是咯咯的笑,接着就是放下碗筷的大笑。
是这样的,老木见他不夹菜,也很少拔饭吃,就去厨房给他拿糕点,那种糯米做的纳糕,还有贴锅饼。
屋子里静极了,灯捻子烧着灯油,有一点吱吱地响。
老木去厨房拿糕点回来,继续吃饭,吃着吃着,皮皮突然就笑了。
我问皮皮笑什么呢?
皮皮说:哈哈,逗死我了。
我问他笑什么。
皮皮说,你瞅,你瞅我大爷吃饭。
我顺着皮皮的手指看过去,烛光下的老木,抿着嘴唇,上嘴唇和下嘴唇紧紧粘贴成一团,同时一前一后蠕动着,还发出吧嗒吧嗒的咀嚼声。
皮皮凑过来,笑嘻嘻地说:看见没?我大爷吃饭真像只兔子!
我说:有什么好笑的,你大爷这几天牙疼,吃东西当然费劲些。
皮皮不乐意地撇撇嘴:人家忍不住嘛!
吃完饭,老木开始提前做灯——为了让我过一个有地方特色的元宵节。皮皮举着松枝条火把,灯火下,老木教我用和好的面,捏成形状不同的灯,用黄豆面做的叫“金灯”,用白面做的叫“银灯”,用荞麦面做的因为颜色较黑就叫“铁灯”。捏好后,放在锅里蒸熟,冷却后倒入豆油,放上灯捻,灯就做好了。
老木说,“送灯”一般在日落星出之前开始,先送到祖宗灵位上,祈求先祖显灵保佑家人一年平安;再送到天地、灶神牌位上,以求神仙赐福家人;然后送到仓库、牛马圈、井台、碾房等处,以求五谷满仓、牛肥马壮,打水平安、粮食常吃常有;最后送到大路口,祈求出入平安,家来四面八方客。
家里的灯送完以后,再由每家的长房长子挎着筐,把面灯送到祖坟上。坟前一般送金银灯,让祖宗在阴间金银常有、荣华富贵。到茔地送灯一定要家里的男孩来完成,女孩不可以——以至于哪家的女人要没生个男孩,到老了连个送灯的都没有。当然这是乡下重男轻女的陋俗。
做完灯,瞌睡虫越来越多地爬到我的身上。这些看不见的虫子,一会儿就把我的精神吃光了,让我像死了一样闭上了眼睛。
半夜,我被老木下炕的动静惊醒。
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老木,干啥去呢?”
“解个手!”
“我也去。”许是兔肉汤喝多了,一觉醒来,我发现自己也憋得厉害。
走出屋,老木看了看野外,说:“啊,好亮!”
我抬头,月亮像一朵微微绽开的花儿,悬挂于乡村空旷的夜空,月光如牛乳汁,整个乡村田野雪地,像被牛乳洗涤过一般,呈现出柔纱般的朦胧。
我突然有种想拎着灯笼,顶着月光,在大马路上悠然漫步的冲动。
我说:“老木,你家的祖坟在哪?”
“祖坟?我爷爷埋的西山岭,我父亲埋在东山岭。”
“哦,分开了,远不远?”
“远,窝在山岭的半坡呢?怎么?你想陪我去祭祖坟?”
“你去我就去!”我看了看远出空旷山野层层叠嶂的山,心一抖,打了个寒蝉,虽然有月光,可现在毕竟是大半夜啊。可当我一对视老木的目光,心就变得无所畏惧起来。
“现在?”老木追问。
“恩!”我紧紧靠着老木,死死拽着他宽大的手掌。
“送灯祭祖坟得元宵那天!”老木说。
“咱就当提前演练!”
“那,咱就不上山,送在道口,咱就往回撤。”
“好!”
正月十五雪打灯,真是应了那句谚语。
月亮像盏大灯笼,挂在天空,照出一条通往山岭的路。我和老木,一人拎着个小灯笼,手牵着手,十指相扣,走在大马路上,仿佛握出了一种幸福的温度。这一刻,手指相间的温暖,永远铭刻在了我和老木脑海。
如丝的月光,像安详、宁静的15瓦灯泡的亮光,水一样流淌下来,照出小路白白的,像是随地扔了条白布。微弱的光线在我心里,比城市的霓虹更明亮,将我脸上幸福的泪痕照亮。
月光如水,我和老木踩着白布似的马路,走着,走着,步子轻缓,且错落有序。导致,之后的很多年,每当我站在月光下,满怀心事看花朵开放,我就会想起这一夜,我和老木,拎着灯笼,十指相扣,走在旷芜乡村的大马路上,成了我生命中最美的回忆。
我和老木不停说着话。
老木说,小时候他过元宵,可有意思了,点着灯笼和爷爷父母去祭祖。那时啊,大多数人做不来原汁原味的灯笼,只能找到一个用过的空罐头瓶子,再用高粱杆做个十字,中间穿一根小铁钉,钉尖向上,小心地放进罐头瓶子里,大小刚好与瓶底相合,做得好的,无论你怎样抛甩,都不会掉出来,然后找一个大小合适的腊烛,用钉尖固定住,最后在瓶口拴一根细绳儿,用小棍挑着,这就做成了当时最最流行的正月十五灯笼会,每个孩子都引以为自豪的主角儿——小灯笼,有条件的还可以在瓶外罩一层彩色的纸。
到了元宵节那天,天刚擦黑,全村的男人都行动起来,每人手里提着自制的灯笼,大人们拎着水桶,里面装着筏头(沼泽地里一种草根,很茂盛,挖出来晾干,撕成一块一块),上面浸满了柴油,大队伍浩浩荡荡向野外下发,目标,祖坟所在地,大人怀着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很郑重地走在前面,而孩子们呢,则多数是为了正月里最后的疯狂吧。
一路走,一路火光,到了坟地里,孩子们载歌载舞,欢呼雀跃着,有的放鞭炮,有了耍灯笼,玩得是不亦乐乎,往往要持续几个小时才能结束。
由此,在乌岭沟当地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元宵节的晚千万别出门,一不留神,就会走到坟地里去,因为这一天的晚上,坟地里是灯火辉煌,远处看,更象一个村落。
老木回忆小时候送灯时的表情很幸福,那副无比幸福开心的模样,让我想起了城里家住小区的那个老人。
我对老木说,我家小区有对老人,可幸福美满了,跑步、遛弯儿、买菜,两人不管什么时候都手牵手,因此大家送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绰号——“拉链儿!”,有时候,哪位有个头疼脑热的,对方摸摸手就能及时发现。
“真的?”老木问,突然加大了力量,手指间的力度骤增,“那咱俩也做拉链儿!”
“好啊!”刚说完,那么一瞬,我鼻子的尾音便又将我拉了回去,如同暗夜里海面一闪而过的灯束,照亮孤寂的小船,之后则又是无边的黑幕。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老木对自己突然很上心,但一种在我看来模糊的东西滋长。因为,我知道,我和老木,不管彼此爱得有多深,但我们注定只能做黑暗中的拉链,充其量,只能在有月光的旷芜乡野,这么十指相扣,忘我的拉上一把。
送灯时,老木站在道口儿,望着东山的山岭,大声喊着:“爹、娘,儿子给你们送灯来了……还有你儿子的兄弟,亲兄弟,小元,韩小元……”
喊完,老木一直默默地盯着灯笼里的蜡烛看,眼看着最后的烛花在烛泪中跳跃,一点一点挣扎着燃烧,烛泪在流淌,老木眼珠上的泪水也在流淌。
送完灯,我和老木站在大马路的道口儿,望着对岸的山和高远的天空,望着很久,老木才紧拽我的手,说:“小元,天冷,咱该回去了。”
我看了看老木,月色下的老木,像着了一层细细密密的霜,
我说:“老木,没想到你嗓子这么好,喊出的声音这么洪亮!”
老木说:“庄稼人的大嗓门,粗!”
我说:“不是粗,是浑厚,好听,你再喊一嗓子。”
老木问:“再喊一嗓子?”
我说:“恩,再喊一嗓子。”
“喊啥呢?”
“你就喊我的名儿。”
“好!”老木双手卷成喇叭状,冲着对面的山喊了起来:“小元,韩小元,兄弟,我的亲兄弟——”声音洪亮,像一声声惊雷从空中砸了下来。
我也学老木,双手卷成喇叭状,冲着对面的山喊了起来:“老木,我的老木,我的亲兄弟——”许是肺活量比不过老木,没喊完,我就呛得咳嗽了起来。
老木拍了拍我的后背:“小元,你话喊多了!”
我说:“那我就喊‘老木’?”
老木说:“好,我喊‘小元’”
“一人一句!”
“老木——”
“小元——”
两人的声音在乌岭沟村野外的夜空久久回响——我和老木,两个男人,大半夜,对着天空,大声喊着对方的名字,这在乌岭沟村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当然,就是放眼全中国,也怕是不多见。
大概是这种前所未有的举动,让我突然雅兴大发,也让我想起那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儿,歌里的那份淡淡思念,淡淡的忧伤和淡淡的温馨让我感动。情不自禁,我唱了起来。
当然,我是为老木唱的。
唱时,我把城里的月光改成了乡村的月光。我唱着:我的心上有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今天凌晨在这个地方,有着对老木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我们在一起。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注定我们能朝夕相伴,乡村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我心房,既然让我们相聚,就让我们多点快乐片段,乡村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你身旁,一年后的今天,让幸福撒满整个夜晚……
唱到老木时,我深情地看着他,唱到我自己时,我就用手指了指我自己。
似乎是受了感染,唱完一遍,老木要我再唱一遍,直至连唱了三遍,老木才说:小元,你唱得真好听!
我说:“老木,想学吗?我教你!”
老木说:“不行,我这嗓子,唱不了歌!”
我说:“你没唱,怎么知道不行。”
“那我试试?”许是受了鼓舞,老木跟着我唱了起来。
虽然,老木唱歌时发出的声音,像是掺进了不少沙子,但并不是说老木的嗓子不好,而是这首歌并不适合老木的这种嗓子唱。可老木唱得不难听,因为老木跟着我唱这支歌时,有种不同一般的虔诚。一个人只要带着情感去唱歌,再不好的嗓子也能唱出好听的歌儿来。
唱完了,我说,老木,你唱得真好。
老木说,不是我唱得好,是你教的好。
我说,我教的好,你唱得也好。
老木说,唱这个歌时,唱到我的心上有一个地方时,我想到的就是你。
我说,真的?
老木说:我就是这么想的!
说着,老木凑过来,嘴唇温柔又温暖地贴到我耳朵根子上,当我的耳垂被老木的牙齿要住时,一股热气吹过我的耳膜,这股热气中散发的柔情化作了一道汩汩流淌的清泉,这道清泉就像是一条没有头的绳子,不知不觉中把我捆了起来,让我的手脚不能动弹。
于是,我靠在老木的胸膛,感觉像是靠着一座山。如果说,老木是山,我是水。那么,山清水才秀,水秀山更清。
我被老木这座山感动了。当然,老木也被周围环绕的水感动了。就这样,老木紧紧抱着我,我也紧紧地环绕着他。似乎还在回味着刚才的歌声。
突然,我的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叫声。
老木听见了,忙问:“小元,饿了吧?”
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许是晚饭汤喝得多,汤这东西,当时喝觉着饱,劲儿一过,饥饿感就来了。
老木不说话,拽着我的手,不顾路滑,一溜小跑着回家。
灶房飘出一股烤肉的香味儿。
我打了个喷嚏,兴奋地说:“哇,好香,有股辣味,什么东西?”
老木一脸神秘:“猜猜?”
我使劲闻了闻:“好象有股肉的糊味。”
老木不说话,笑眯眯跑去锅灶。
我赶紧跟过去。
我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锅内一排排串好的烤肉,像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竹排,躺在锅内,散发出油亮的光泽,一股浓浓的香味在厨房四周弥漫开来。
“老木,什么啊这是?”
“夜宵啊!”
“好啊,老木,原来昨晚你是存心不让我吃饱!”我捶了一下他。
“小元,想吃什么口味的?味道可以自己选择调料粉,这儿有孜然、有胡椒粉……”
月光泻入炕沿,炕上的小方桌,我和老木,就着窗外的月光,吃着香喷喷的烤肉。
老木问我吃过烤野兔子肉没有,我摇摇头说没有吃过。
老木把一条兔子腿递给我,我吃了一口说:“恩,好吃,真香!”我不知吃过多少酒宴,可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老木说:“还有更香的呢?”
老木说,小时候,他经常从火炭灰里扒出青苞谷棒子,像剥大葱一样剥去层层裹着的皮,露出了烤熟的苞谷籽,一粒粒像玉一样饱满光润,腾腾的热气里一股清香扑鼻。咬一口,有奶一样的汁液溢出。
老木回忆小时候的样子竟有了点小孩子的天真劲。
老木说:“小元,要不咱俩把桌子搬到后院菜院吃去?”
我没明白过来,摸了一下老木的额头:“老木,不会吧,多冷啊,还有风,点不了蜡烛的。”
老木说:“有灯笼啊,还有月亮……你不是说要过一个‘吃着烤野兔肉,看着月亮,数着星星’的元宵节么?”
我一楞,突然想到自己在电视里看到的情节。
原来是这样!这个老木,真是受不了,随口这么一说,真就跑去逮野兔了,真就给我做烤肉了。
我不敢看老木,别过头看窗外。月光像凝望回忆的眼神,像拂过心田的温馨。月光如情人的眼眸,柔柔地,浸润我渴盼的心田。
这是万人安睡的夜晚。窗帏低垂,夫妻交颈,少年美梦,婴儿呢喃,被褥温热温热,时钟滴答滴答。
吃完烧烤,却睡不着。我躺在炕上,透过窗,能看到老木菜园子上方一片大大的天空。月亮像是天空的眼睛,你看它的同时,它也在看你。它的目光从窗外钻进来,不但要爬到你的床上,爬到你的身上,还要爬到你的心上。
水银似的白月光,透过未合拢的窗帘,泼泼溅溅,抛洒在炕前,我在半明半暗的光影里,凝视着老木的脸,那低低的鼾声,幸福就如荷叶上的露珠,澄澈饱满,一颗一颗滑下来,积聚成一汪水,在我的心底摇荡。
想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情不自禁地,眼角就湿成了一片。
上帝给谁的都不会太多!突然,我想起这么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说是新加坡旅游局给总统李光耀送了一份报告,大意是说新加坡不像埃及有金字塔,不像中国有长城,不象日本有富士山,不像夏威夷有几十米高的海浪。新加坡除了一年四季直射的阳光,什么名胜古迹都没有,要发展旅游事业,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李光耀看过报告后,非常的气愤,在报告上批了这样一行字:你想让上帝给我们多少东西?阳光?阳光就足够了!后来,新加坡利用一年四射的阳光,种花植草,在很短的时间里,发展成了世界上著名的“花园城市”,旅游收入连续多年列亚洲第三位。
是啊,既然上帝把我变成了同性恋,让我失去了很多。幸运的是,上帝还给我送来了老木。上帝的馈赠虽少得可怜,但它却是酵母。人在这世上走一遭,没有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是幸福,如果有来生,如果还拥有老木,我还选择自己是个gay。
以前。我常常羡慕那些有过人的智慧、成绩优异的人,以为出类拔萃的人就是幸福。然而,我现在觉得这样的人往往并不幸福,因为他们常常以优秀自居,常常有舍我其谁的不平和,常常是愤世嫉俗,最后自然觉得与幸福无缘。我还以为那些不为衣食所忧,天天过着杂志一样的生活的大款是幸福的,其实不然,他们仍不满足……现在,我躺在老木家的炕上,顶着月光,看着酣睡的老木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终于明白,守着自己相爱的人,按自己的愿望安排自己的时间,过平淡的生活,不为金钱折腰,不为虚名所累,这就是幸福。
投稿请发往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