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三万元了结了这事。
大丰呢,也被他所在的YY中学开除了,而已顿感绝望的父亲把他送去了Z市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学起了当时炽手可热的电子技术。
事情经过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我在县城多呆了三天,大丰一直没回来。我决定回龙溪。我是带着复杂心情回龙溪的。
龙溪中学的初一、初二还没放假,我只去找过小康一次,叫他上我家吃了顿饭,他马上要期末考试了,我不想他分散精力。
我的中考成绩还没出来,其实分数出不出来,结果已经出来了,题目简单得像吃豆腐,我至今还对父亲送我去县城读书的必要性提出质疑。
在小康假期补课的前几天,我天天去找他,有时一天找三四次,理由很多,诸如上我家吃饭呀,陪我去蓝河滩散步呀,我很是想你了呀。然后借机骚扰他。
当然只是在没人时接接吻,拥抱拥抱,我家人多,二姐经常牵着她的儿子过来,三姐也在家住,大姐也时不时从县城回来(她在我中考前三个月搬去了县城住,帮姐夫打理他在县城的生意),甚是热闹,有些事情,就是想做也做不了。我开始有点猴急上火了,我想小康呀。
补了六天课后,小康要我和他回云泉。我很是惊讶,问他:
“不补了?”
“放假一天。”
瓜棚还在原来的地方。只是今年小多了,还简陋,甚至没挂苇帘。小康把早已准备好的编织袋撕开,把瓜棚四周裹了个严严实实,像个封闭式的小帐篷。
小三当然不能让他跟着去了,这次理由还过得去:瓜棚太小,挤不下。
我想,我真是对这一天期盼很久了,从小康家出来,走在云泉村的路上,我的老二就一直硬邦邦的,难受极了,幸亏是只听其声不见其影的傍晚时分。
小康提着准备好的东西,我双手从背后搂着他的腰,下颚磕在他的肩上,走一步我说一句:小康,我硬了;小康,我难受;小康,亲一口。
小康摘了一个大西瓜,进棚,放下瓜,我抱起他就往搭好的床架子摔。
小康说:“涛子,别心急,啊,哥哥先把床铺好。”语气甚是轻柔,简直不像他发出的声音。说着,他麻利铺着毯子,铺好后拍拍手,扑通倒在了床上。
“亲爱的,来吧”他伸出了手,“今天晚上就是被你咬死了,掐死了,我也不吭半句。”
久旱遇甘雨,烈火烧干柴,我像是得到了发号令,一下猛地扑了过去。
我把手插进他的头发,胡乱楸着,咬他的嘴唇,伸出舌尖插入他的嘴,像条受伤的曼鱼,疯狂在里面挣扎、跳跃——我要把这近一年的想念和欲望在这一刻统统爆发出来,彻底的、疯狂的、无所顾忌地,爆发、爆发、再爆发。
我笨手笨脚为小康脱着裤子和衣服,我那个急呀,小康轻声吼了吼:涛子,撕,痛快地撕,今天晚上你想怎么着都行。
好,撕,我撕!
我急不可耐,肆虐扯他的裤头,撕他的衣服。
当他身上所有的东西被我撕得支零破碎,所剩无几时,我趴在他健康光滑的肉体上,开始吻他的脸,吻他的胸,吻他红红的小乳投,吻他的肚皮、小腹,还有荫毛。
突然发现,小康比以前健壮了,变得性感了。
荫.经又大了些,嫩嫩的亀头似乎还有些羞涩,一半卷缩在包皮里,一半露出来,对着我浅浅地笑,那笑,还有点挑衅。
小康的荫毛也增加了不少,长了,多了,还密了,我疯狂地亲着他的荫.经,吻着他的荫毛,着迷、贪婪、痴恋地呼吸着从里面散发出的气息,一个男人特有的气息。
小康兴奋了,剧烈喘息起来,还叫着我的名字。
我也兴奋了,大口换着气,回叫着他的名字。我们死死掐抱着,狂热扭动着、挣扎着。
我感觉自己的灵魂和躯体同时被一股超强的回旋气流吸住,再慢慢卷进去、卷进去,随之来到了一个从未去过的奇妙世界,这个陌生的世界里,欲仙欲死、如痴如醉。我搂紧小康的脖子,用力咬他的唇,呼喊着:小康,小康,喊了一遍又一遍。
我的肉体呀,我的灵魂呀,即使翻编所有的中华大字典、大词典,我也找不出任何词汇来描述我当时那种灵魂超脱肉体的极度快感。
我只记得,我的灵魂瞬间脱离了肉体,在一个奇仙异境飘呀飘,飘着飘着,我就猛地大声喊了最后一句:小康,便死死地趴着,一动也不动。等我的灵魂重新回到肉体,我才意识过来,我是趴在小康身上,正死死搂着他,掐着他的肩膀。
我身寸.米青了——我真的身寸.米青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身寸.米青了,只记得当时在最极度的快感过后,我把小康搂得紧紧的,一动也不动,生怕小康突然从我身边飞走。当小康动了动身子,我慌了,急了,他要飞走了吗?我又开始赶紧吻他的脸,吻他的胸,吻他乳投,吻他的肚皮,吻着吻着,突然吻到了黏糊糊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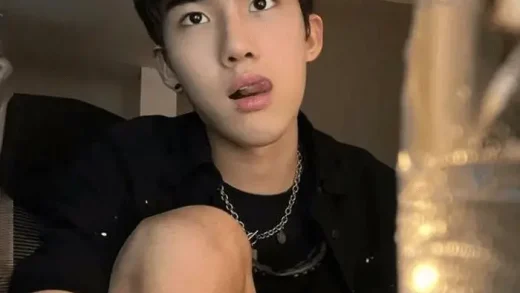

鲍小三太可怜了
看一次哭一次,太催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