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而外,还有个原因。
有一天,田老大发现,看房团里有个熟悉的身影。似曾相识,又不记得究竟是谁。正纳闷间,那人也发现了他。迟疑了一下,走上前来,问道:
“你也来买房啊?”
“啊!”田老大胡乱应了一声,很装蒜地翻了翻手里的楼书折页道:“过来看看,听说还不错。”转身看看那边鱼贯而入的准业主,又道:“好久不见!”
“是啊,快两年了!”
“喔。”
“什么时候再聚聚?”搓着手。
“呵呵。”
“笑起来还是老样子啊,哈哈!”
啧啧,好暧昧!
这胖子虽然细皮嫩肉、气质儒雅,可是那两只眼睛里总充溢着一种深不可测的**,炽烈如火,愣是让田老大这样的欢场老手也难免怯场。
靠,难道我过去和他有过一腿?
看这样子,还不止一腿。
田老大依稀记得他是个老客户,而且看来满意度颇高。只是不知何故断了来往。现在重拾旧好也未为晚矣,至少可以拿他练练枪。于是,留了个业务电话给他。
“欢迎来搞!”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胖子不到四十岁,走远了田老大才想起来,好像是一家电视台的什么干部。俩人曾好过一阵,胖子光顾了他小半年,后来实在资金吃紧,就打算与别人搭伙,自然,月费是要降低的。田老大当时没同意,因为觉得有点乱。
不过,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
乱一点没关系,只要钱给够。
在他们俩说话的当口,何方正没有过来打扰。不过,他远远地看见了,从他们的表情里,读出了一些内容,心里不免有些不快。回去的路上,他一言不发,有些怨怼地不时看两眼田老大,恨不能捶他两下才好。
却又爱得要死。
那突出如山峰般的喉结,那硬扎扎的络腮胡,硬朗的面庞,奇峻的大鼻子,薄得恰到好处的润泽的唇,手上粗大的关节和暴突的筋脉血管,甚至鼻毛,甚至吐痰时“嗖”的一声几米远的力道,都让何方正恨也恨不起来。
在街边餐馆里吃了晚饭。
何方正提议去酒吧玩,田老大照例否决,理由还是怕老婆电话查岗,不见人在,会出事情。好吧,那个神秘的从未见过一丝踪影的老婆大人,看在她的合法身份的份上,就忍耐一下吧。只要能亲近这个男人,一切都不在乎了。
半夜,正**间,一个电话打来。
“嘘,查岗!”示意别出声。
何方正有点小生气,又不敢真发火,就把不满全都撒在田老大的小弟身上。是啊,惹不起老大,还惹不起老二么?他像拔萝卜一样轻使蛮力,揪那只大萝卜。
被田老大的大手打了回去。
可是真疼呢!
悻悻的。
“呵呵,是你呀,我当谁呢!怎么,还没睡觉……哈哈,你可真幽默……有胆你就来,谁怕谁呀……说实话?说了你可别生气,我还真把你名字忘了……不是不是,我哪敢哪,只是我脑子笨,记不得人名字。噢,姓袁……好,小袁……”
真肉麻!
这算什么,当着我面儿和别人**?
何方正,你有点骨气好不好!
我可真生气了,真生气了呀!好吧,揪你的黑米米,吸血鬼一样咬你的脖颈,咬死你为止!
田老大一看:“我靠,要造反啦!”
张开两只大手,就去撇开何方正这只发疯的小兽。
何方正不依不饶。但即使如此,他也没真下力气咬。他的牙齿在那让他又爱又恨的男人身上舍不得下力气,最后那些恨又变成了放任的爱,在肩胛肉处轻轻咬合,留下两弯浅浅的牙印。不止肩胛处,还有脖颈处,黑米处,也都留下了他痴迷又彷徨的牙印。那些牙印就像一张张小嘴,在嘲笑他的有气无力。
“你疯了!”田老大用力推倒他。
何方正像只原木一样,从双人床滚落在地毯上。
吃吃地笑,不作言语。
“还笑!”田老大心有余悸地摸着那些深浅不一的牙印,道:“你傻呀,还真下得了嘴!”
“大不了你再咬回去!”
“我又不是狗。”
田老大是真生气了,气得宽大坚实的胸膛起伏不定,要是用内窥镜看看,那颗不知是黑是红的心,肯定在砰砰砰乱跳。难道他是真怕我把他咬死么?倘若我是真想咬,不要说是几排牙印了,连那条大萝卜也一起连根拔起了。
何方正被推下了床。
索性就不起来。
好吧,你不是狗,我是狗。你那么好,我怎么配得上你。虽然爱你爱到了骨头缝,可恨你也恨到了牙痒痒。我何方正虽然说不上什么为人师表,可好歹也是一个人民教师,一个知识分子大学生,一个有脸面的人。你既然弃我如敝履,对我的感受毫不在意,把我当空气当牛做马,我……我干脆走了算了。
何方正也恼了!
从地毯上爬起来,就去拾自己的衣服。
那些衣服横七竖八地撂在沙发上,一片狼藉。何方正突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后悔,后悔自己如此不争气,把自己满心期待的爱情交给这样一个没心没肺的男人。后悔自己经不起**,半路改道,放弃了苦守多年的原则和底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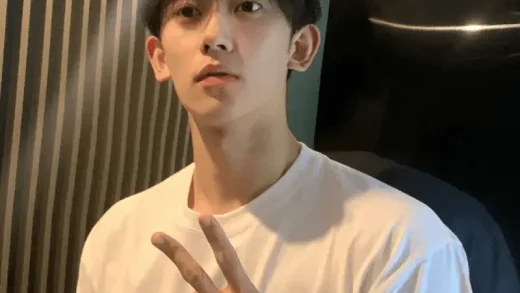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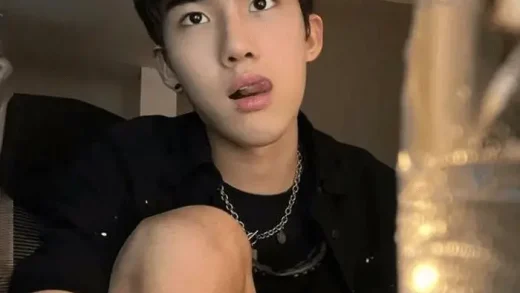

后面没有吗?挺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