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他发现。
那人二十来岁,斯文儒雅,书卷气十足。
一副金丝眼镜,反光的镜片,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神。
但张伟明知道,自己被他注视着。
冷笑,只是因为得意。
得意洋洋。
一般来说,得意忘形的人,表现欲都特别强。张伟明用一支兔子舞来表达他的得意,不过很可惜,这只兔子被误解为伤心过了头,所以才会表现出如此夸张的快乐。舞曲结束,大堂和他击掌庆贺,又为他倒了三分红酒,二人一饮而尽。最后,大堂递给他一张纸条,努嘴示意,是金丝眼镜的。张伟明展开纸条看了一眼,字如其人,秀气而工整。
一丝不苟。
“怎么样,过去看看吧?”大堂戏谑道:“那么闷骚一个人,难得主动一回。”
“你认识他?”张伟明笑道。
“最近常来,可能是春节没回家。听说是个老师。”
“噢,为人师表!”诡笑。
“得,见不得你这笑!”大堂叹息道。
“一见你就笑,不好吗?”
“你一笑,就有人要倒霉,咱是既羡慕,又同情,五味杂陈啊。”
“难道,你也想倒霉?”
张伟明很阴险地笑着,来了个老鹰掏小鸡。本来只是想装腔作势,闹一闹。不料想,大堂竟然不躲不闪,以一副大无畏、慷慨就义,佛祖割肉喂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迎接他的爪子。张伟明出乎意料地抓了个饱满,先是一愣,既而大笑:
“**!”
大堂一副委屈的样子,真真假假。
不理你了!
“快去,人家已经等不及了,嗯……痒得难受哩!”
“去死!”
闹也闹够了,张伟明欣然前往。
本来,他对这种小公鸡是不感兴趣的。不过被人传纸条,还是第一次。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过去看看也无妨。
“才来呀?”张伟明问道。旁边挨着坐下来,往一空杯子里倒酒。
是啤酒,白色的沫子快速涌起,像潜水的呼吸。
“啊,你说什么?”金丝眼镜没听清。
音乐振聋发聩。
“我说你‘才来呀’。”这回贴着耳朵喊。贴得这么近,能嗅到彼此衣服上的气体,猜到对方经常使用的薰衣草,洗澡用的沐浴液或香皂是什么香型,牙膏是薄荷还是草本,身体内循环是否调理得当。
还有团团的湿气,热乎乎的。
熏了耳廓湿润润的。
“啊,有好久了!”这回听到了。
“做什么的?”张伟明把一只手压在他腿上,能感受到里面毛裤的纹理。
盯着他的眼睛,貌似痴痴的,花痴?
“这么快呀?”腼腆地笑起来,但还是得回答:“1、0都可以的。”
他显然没说实话,这是留着后路呢。
“我没问你这个,我是说你做什么工作的?”
“啊,我还以为。”囧死了,汗。
“你以为什么?”暧昧地笑。
“我是个老师。”
“难怪,这么斯文。”窃笑。
**着他的手,软软的,灯芯绒一般。
张伟明有种恶作剧的**,他虽然阅尽春色无数,可还没玩过老师呢!一想到在讲台上为人师表的老师,将成为他胯下冤魂,他得意地几乎要笑出来。而这个可怜的小兽,显然已经被他完全捕获了,不费吹灰之力。
又说了无边的话。
喝了几杯酒。
张伟明确信,这时候要上他,不可能被拒绝。
哪怕是再矜持的人,也会把底线忘掉。
于是,冲服务生打了个手势。
OK,结账走人!
旁边就有酒店,但是开房间要身份证,张伟明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于是,他开车载着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的老师去田老大暂时居住的房子。路上,俩人并排坐着。金丝眼镜不时扭头看看他,然后腼腆地笑笑。这样的动作重复了N多次,既陌生又熟悉,让张伟明良心发现,突然有点于心不忍了。他想起了王石头第一次坐他车时,笨拙的样子,那样子深深地刺痛了张伟明的心。倏尔又想起在颠簸的马自达里,强吻王石头的那一幕,以及临别时,王石头怅然若失的样子。
他恶作剧的冲动突然消失了。
在一路口缓缓停下车,饱含歉意地说:“小何,对不起,你走吧。”
“啊,你,什么意思呵?”
“实在对不起!”
“怎么回事,有哪里不对吗?”
“不要问了,可以吗?”张伟明从钱包里掏出两张百元大钞,塞给小何老师:“你打车回家吧,实在对不起!”
“你神经病啊!”小何老师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因为气愤,而又不愿意轻易破坏他一贯严谨的形象,他如贝壳般整齐的牙齿把嘴唇都要咬破了,颤抖了好一会儿,才骂了这么一句。他一把抓过钞票,狠狠摔在张伟明脸上:“有钱了不起吗,有钱就可以随便耍猴玩吗,啊?”
“真是莫名其妙!”悻悻下了车,“嘭”地甩上车门,又补了一句。
“实在对不起!”张伟明歉疚地说。
车忽忽开走了。
张伟明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
面对**,他决定忍耐。
有时候,忍耐也是一种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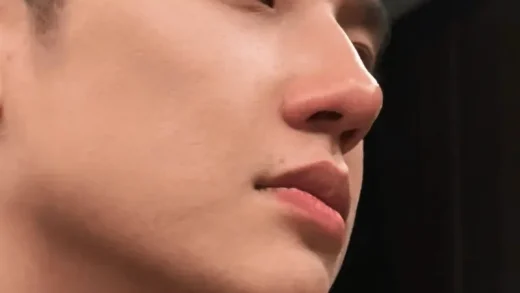


后面没有吗?挺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