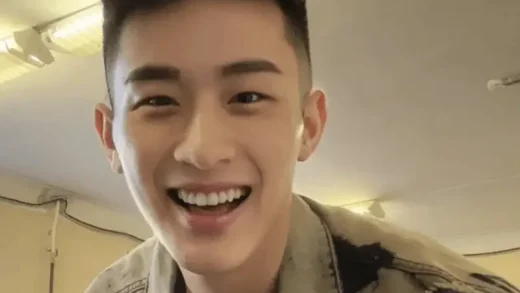这几天回广汉一家人住宾馆。本来他二姨说喊住她屋头,新房子也够宽敞。但高升平晓得他老汉看不惯二姨一家的做派,大姨屋头房子窄又住不下,所以早就在网上定好了房间。今天到广元他直接把妈老汉安排到了宾馆,放下东西后,自己借口买烟下到楼下。
说是买烟,其实是打电话。拨通之后就听到那头沙哑疲惫的声音问到,“你还想得起我诶?这们久才回我电话。”
说话的正是张海波。上次两人见面还是褚健请喝酒的那天晚上,这几天高升平特别事情多,压根没想起张海波来。刚才开车也不方便接电话,所以张海波一问,他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特意关心地问到,
“你哪门了诶?病了说?”
“看病没得诶?”
“嗯,都要过年了,快点好起来。好回老家过年。”
听到这里,张海波在电话里头哀嚎起来,“我哪里还有老家可以回哦!离了婚,像过街老鼠一样。我妈老汉肯定要给我重新介绍!”
“那你就继续去相亲嘛,总会有合适的。”高升平缓缓地劝说到。
“不想去相别个了。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张海波忽然正经了起来,“要不,你还是把我收了嘛,正儿八经那种收了。我们两个都不去找别个了,好不好?”
晚饭在立峰大酒楼二楼请客,地方是高升平事先选好的。
一个装修得很喜庆的大包间,足以容纳二十来号人。旁边连着个小包间,还可以坐十来号人,足以容纳高育仁陈红兰两家的亲戚。老高夫妇则穿着儿子事先准备好的喜庆唐装,红光满面,迎客送宾,好不热闹。
“二弟二妹,你们来了啊。”
“哦,这是秀春的娃儿啊,都这门大了。来来来,大爷爷大婆婆给个红包。”
“三老弟,你也来了啊!”
“哦,我好得很,没得啥子事。就是麻烦你们都坐车出来,好多年没看到你都嘛。”
高育仁搂抱着自己的骨肉兄弟,喜不自胜地说到。
“二姐。”
“哎呀,不收红包。”
“喂,老高,二姐要送红包,你快点帮我塞回去。”
“来来来,小东西们,这是小姨婆小姨公的红包。没拿到的等哈哈找平叔叔要。”
陈红兰推搡着自己的血亲姐妹,催着大家快点坐定。
高升平在一旁拎着烟酒糖果红包袋,见人就发,见人就撒。这次回广元,他老汉说是双方的亲戚都要聚一聚,图个过年热闹喜庆。其实高升平晓得他老汉的意思,就是生怕这回下不到手术台,所以想来个提前告别。
他妈陈红兰吓得不得了,悄悄把高升平拉到一边说你老汉搞这门大的阵仗是想做啥子哦,未必他就等死了啊?高升平劝慰说古代还有冲喜这种说法,你就当冲喜了嘛。再说老家亲戚的确好多年都没有见全过了,你就当合家欢乐,莫去多想。二嬢大嬢要是问起原因,你也莫多说。
一席人纷纷坐定,年轻人和小孩脸上都洋溢着新年到来的欢乐情绪。只有老的那几个在一起交头接耳,脸上有些隐藏的忧郁。只听得玻璃杯当当当被敲响的声音,老高从席位正中间站了起来。他一手高举着酒杯,一手按在老伴陈红兰的肩膀上,笑着对大家说到,“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百忙之中赏光来吃我屋头这顿团年饭。特别是我,今天要感谢大家。”
说到这里,老高停下来环顾了一遍左右,才接着说到,“小时候屋头穷,但是有兄弟陪伴,成天上山打猪草放牛烧苞谷红苕,所以我不觉得造孽。成人后工作累,但是有兰兰陪伴,她成天端茶烧饭帮我生儿育女,所以我不觉得辛苦。后头……”
此时身旁的陈红兰早已泣不成声,她紧握着老高搭在自己肩上的手,不忍再听下去。高育仁自己也开始哽咽,但他还是勉力说到,“如今啊,我得了这个病,后头真不好说。我儿升平娃儿已经长大,自己谋得到生求得到饭吃了,我都不担心他了。我唯一放不下的,就是这个老婆子。要是万一真哪们个了,”
说到这里,他用力拍了拍陈红兰的肩膀,然后眼含热泪地向着陈红兰的大姐二姐说到,“大姐二姐,就要麻烦你们多费心、照看一哈了。”
高育仁虽与陈红兰是结发夫妻,但年龄着实比陈红兰要大上一截,因此他从不随陈红兰称呼大姐二姐,只以姓名相称。今日这般刻意称呼,言下多有托付之意。一旁的高升平听在耳里,难过在心里。
但今天的确不应该是难过的日子!姑且不论此时宾客满座,就是年后老高手术的成功几率,也是不低的。所以高升平迅速掏出一沓红包递到父母手中,又怂恿小孩子们纷纷上前讨要。自己则招呼上菜传酒,照顾亲戚故旧,过大年的光景瞬间热闹旺盛了起来。临到酒席结束,高升平望着坐在亮黄灯光中的父母,有种特别慈祥亲切的模样,不觉鼻头一酸,泪水涌出眼眶,悄悄滴落在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