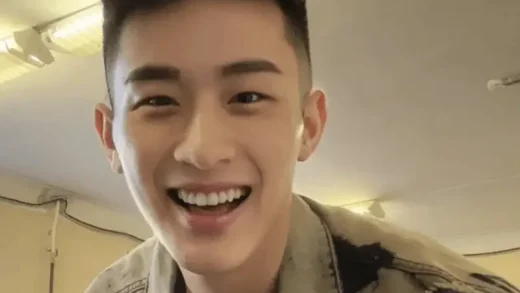可能是回四川这几天没开到车手痒,王建军主动说去眉山来回由他负责开车,对此高升平自然是喜闻乐见,巴能不得。只见王建军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在高速路上把这辆白色小车开得又稳又快,仪表盘根本就没下过100。做到他熟悉的事情,王建军的话明显多了起来。
“高升平,你这辆车油跑得不够啊。”
“啊,开了五年才这点路程啊。车就是要多跑路啊。”
“不行不行,你的车用得太斯文了。根本没有把车的潜能调动出来。”
“你什么时候有空嘛,去阿克苏。我带你去戈壁滩上开越野,加足马力乱跑都没得事。”
高升平笑着听着,心里觉得眼前这个话说不停的王建军,离童年时那个从大漠归来、有讲不完异闻趣事的小男子汉,又更近一步了。他看着窗外群山叠翠,薄雾环绕,午后的阳光既不耀眼也不炎热,全身懒洋洋的。过往的回忆与耳边的现实交汇,思绪开始散漫了起来。
只见王建军那张黝黑的大脸,就贴在高升平眼睛跟前,两人之间的距离只有0.1毫米。这么近,以至于高升平看得见他眼角每一条皱纹的走向,和感受得到他口鼻间喷出的炽热乱离的气息。高升平咽了一口口水,想了一下,就歪着头吻了上去。厚实的大舌头像刘小兵,口水汁液的甘甜又像张海波,完美的吻感让高升平唤起了久违的激情。他一把扯开王建军的衣服,肆意地抚摸和拥抱着这陌生又熟悉的身体。比刘小兵柔软一点,比张海波又健壮一点,下半身有一截粗壮隐藏在茂盛的毛发里。高升平一把抱住就想来个颠龙倒凤,但自己下半身好像裤子没有脱掉,勒得难受。他一边心里暗骂这破优衣库的裤子就是不好穿,便宜无好货。一边尴尬地看着王建军笑着,生怕事没成人就走了。不成想那王建军说还有事要去社保局办,转身要走。高升平连忙招手,喊他不要走。但王建军越走越远,影子都快看不见了。高升平只觉身体被绑住,想追上去却动不了,旁边还有人不停挤他。
“高升平,高升平,莫睡了。”
高升平迷迷糊糊间听到有人在喊着他的名字,还用手在推他,心想这是谁不识相,赶着来坏我好事。待努力睁开眼之后,才发现车已经停了下来,自己还绑着安全带坐在副驾位置上。一旁的王建军笑笑地看着他,手上轻轻用力,正想推醒他。
“这是哪里了哦?”高升平带着梦呓的声音问了一句。
那头王建军声音含糊不清地回答说,“居平休息站,抽根烟,休息一会再接着开。”
“哦”,高升平伸了个懒腰,想坐正了再下车,却瞥见王建军的眼神有点怪怪的。他下意识地往自己下半身看了一眼,有个不雅观的凸起,非常明显。
高升平惊呼了一声,一瞬间清醒了过来。只见他一个弹身坐正了身体,丢下一句“我去上哈厕所”,就曲着腰打开车门,飞叉叉地跑了出去,把王建军一个人尴尬地留在了车里。
王建军父亲虽然死了,但他父亲的大哥,也就是王建军的大伯还活起在。老人家年近八十,精神劲足得很。看到二十多年没见的侄儿王建军,那个激动啊,让身为旁人的高升平都忍不住热泪盈眶。还是小娃儿的高升平,曾经和王建军一起来他大伯家耍过。这么多年没见,老人家记性好得很,依然晓得高升平就是那个怕热的小胖子。
两人到眉山宝华镇的时间点,刚好下午五点过。由于来之前打过电话,一番简单的寒暄后,屋外的坝坝宴就摆好了。王建军的大伯二伯屋头、堂兄堂妹这些,统共二、三十口人,坐了满当当的三大桌。
农村吃饭就图个闹热人多,酒不一定好但管够,菜不够精致但包管新鲜。高升平被连灌了几杯红毛烧下肚,直接就喊打脑壳了,遭求不住。那头王建军倒是稳得起,来者不拒,连说带喝,上了桌子就没停过。
高升平本以为这次陪王建军回乡,应该是一趟伤怀之行。未曾想死去的人的悲苦,比不上活着人简单的快乐。那最深沉的悲伤,恐怕也只有留给最亲的亲人,去久久咀嚼缅怀。
但这样也挺好,至少王建军喝了酒以后,那个红光满面的精神气,就一点点地释放了出来。他本来就是个性情爽朗、外向好玩的质朴人,这么些年照顾父亲,人前做些俯首迎接的简单工作,人后煮饭洗衣琐碎无比,生活渐渐变得沉闷保守,性格也事事求稳。现在父亲亡故,悲痛之余,人却放松了下来。那个被压抑许久、未曾真正舒展过的真性情王建军,也一点点地活了过来。
高升平见酒席上那个高声畅谈、大口喝酒的王建军,心里暗自赞许,觉得这才是那个自己多年性幻想对象的军哥嘛。正思索间,一碗酒端到了跟前。抬头一看,原来是王建军的堂兄。这个堂兄在外头包工地,早早地在眉山买了房子,今天是为了王建军回乡,特地从眉山开车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