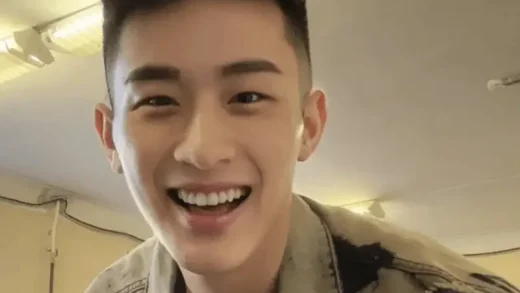“那你去喊那个强巴给你看过没得诶?”
“有啊,看过的。”
小周有气无力地回答到,他年轻英俊的脸上,不经意地闪过了一丝阴霾。
“那你看到啥子诶?”高升平追问到。
“我看到啊?我看到了蓝天白云,看到了雪山草地,我看到了……”
本来没个正经、正疯疯癫癫的小周忽然打住了话头,高升平见他笑容凝固在了嘴角,眼神也变得温柔了起来,于是顺着目光往前看去。那个叫扎西的笨小伙子,此时正帮村子里的一位老奶奶从牦牛车上卸货。他那朴拙的身姿与爽朗的笑声,于无意间挥洒着男性的魅力,竟然令人有着十二分的心动。高升平见小周望着扎西的眼神都痴了,心想这也是孽缘了,不禁偷偷地叹了口气,
“那扎西有没有喊强巴看哈诶?他那么糊涂的人,看哈可能还比较有用处。”
小周并没有回答高升平,只是继续出神看着前方,嘴里嘟嘟囔囔地碎碎念到,
“我才不信啥子命诶。只有和我在一起,才是对他最好的。”
下午的时候,高升平趁没人把扎西拉到一边,问强巴有没有给他看过梦陀罗。扎西笑嘻嘻地答到,
“师兄,你到底看到啥子了哦,遭黑(吓)成这个样子?”
“没有啊,没看到啥子奇怪的诶。我只是问哈你,人家小周都给我说了都嘛。”
“是不是哦?我问他他都不给我讲看到了啥子,居然给师兄你讲了?”
“别那么多废话,你到底看到啥子了?准不准?”
扎西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说出了句令高升平大跌眼镜的话,
“切,你小子,居然敢豁(骗)我。”
高升平愤然拂袖离去,只剩下扎西在身后反复申辩到,
“师兄,我真的没豁你。哪个儿豁你嘛,真的没给我看过……”
这次回甘孜工作十来天,张海波就打过两、三回电话。其中一次还是高升平打过去没接,随后回过来的。特别是后面这一次,高升平听他说话有气无力,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张海波说不是,只是最近事情有点多,太累了。高升平笑骂到,
“那你龟儿子之前还扯把子说要来康定找我?找个锤子啊,来了日都日不动了。”
张海波像断了气一样跟着呵呵了两声,然后才恨恨地说道,
“那不得行!日你肯定还是日得动的。”
临到挂电话时,高升平生生地把张海波喊住,
“真有啥子事情莫瞒到,说出来大家帮到想想办法,不要自己憋到起。”
“嗯,我晓得了,我晓得了。”
不知怎么的,最后张海波说话听起来居然有点哭腔,高升平看着挂断后尽是忙音的电话,独自陷入了沉思。
跑完康定附近乡县,就该往更远的地方进发了。高升平看着国道318上蓝色的路牌写着离拉萨还有1200公里的时候,居然没有遥远的感觉。
理塘再往里走,就是稻城亚丁,按理说这大名鼎鼎的风景区应该一马平川,处处坦途。但高升平他们支教小组专门去那些夹沟里村落,一间学校与一间学校之间虽然只隔着一座高山,却常常要费上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再加上路上多是些粗糙未修缮好的土方路,时常有塌方落石阻碍行程,艰难困苦,难以言说。
高升平知道自己这组,只是数百个在藏区支教的小组中的一支。成千上万的人,都将开启智慧教育的重担,担负在自己肩上。高升平只是无意中搭乘了这趟绝地列车,但心中的自豪是一天强过一天。
这种感受他告诉过王建军,王建军表示非常理解。毕竟在他父亲那一辈,正是在支援边疆的口号下,才去了遥远的他乡,挥洒年轻的生命。直到最后他乡变成故乡,在荒漠戈壁滩上埋葬了衰老的身躯,与自己相爱的女人长相厮守,说起来居然有几分浪漫的感觉。
高升平本想说若是军哥你和我一起来这高原驰骋,那也的确挺浪漫的。可这一句玩笑话到了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倒是王建军坦坦荡荡地说到,要是来了甘孜,一定帮高升平开车,让他什么都不必担心地观览这极地风光。
这一日众人离了水洼乡,打算晚上住在香巴拉镇。没想到路过尼斯山的时候,遇到峡谷里山体塌了方,车只得在路边停了下来,等待前方公路队清路。王干事廖老师他们三个,缩到路伢子上抽烟去了,高升平有点晕车,独自坐在路边的防撞柱上休息。小周和扎西两个小家伙没心没肺地跑到前面去看公路队爆破大石头,高升平本想喊他们莫去凑热闹,但身体不舒服嗓子发炎,再加上今天上培训课说了整天的话,此时竟没力气再多说几句。只得看着两个年轻的身影越走越远,在暮色暝合中渐渐变得有些模糊。
此时山谷里的风好像停住了!周围一切安静得那么绝对,连鸟儿翅膀扑棱的声音都听不见了。高升平觉得额头发紧,耳朵发烫,心里忐忑不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