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这边过年吗?”志强问我。
“嗯,回来!”这么多年了,我还是比较愿意待在这边过年,家家户户都喜气洋洋的围坐在一起吃饺子,邻居亲戚相互串门拜年送礼,孩子们追逐打闹放鞭炮烧烟花,那种浓烈的节日气氛早已成为我心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记得带个北京妞回来!”他俩笑着说。
这是我上车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汽笛长鸣,黄绿色铁皮车缓缓地开出站台,我痴痴地看着他们逐渐变小的身影,心中微感失落。
四个月零两天了……
* * *
与母亲上一次见面已经是半年前,所以这次母子重逢,我固然开心,却也远比不上她的激动与兴奋。
袁叔叔知道我要过来也很开心,一早就给我准备好了床铺,让我和小杰一块住。
小杰和他的姐姐雪萱也已经放假了,于是袁叔叔让他们俩陪着我在北京到处去逛。
雪萱年纪比我小四岁,现在在念高三,准备明年考大学。
听母亲说,她刚接触雪萱时,雪萱对她非常抵触,后边足足花了五六年时间才逐渐认同她这个继母的身份,到现在也只是叫我母亲郝姨。
她跟志杰比较要好,对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十分疼爱。
我到了北京之后,她就与弟弟一同陪着我去游恭王府、颐和园,又拉着我到东直门簋街、王府井、护国寺去尝北京地道的炸酱面、卤煮、驴打滚、炒肝等小吃,而袁叔叔也抽空和我们一同去全聚德吃北京烤鸭和涮羊肉,还去小汤山泡了一次温泉。
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再过两天我就得回去。
因为前两天刚下了一场大雪,今天上午开始转晴了,所以雪萱建议我们三个人一块去北海溜冰。
没想到北海公园里来溜冰、玩冰球的人还真不少,而且溜冰的人男女老少都有,有的老人家玩得比年轻人都好,几乎是满场地飞呀、转呀,还做出起蹲转圈,前跳后跃,背溜曲滑等各种花样动作,看得小杰在一直在拼命鼓掌欢呼。
我的溜冰技术不怎么样,只能保证在不摔跤的前提下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雪萱倒是玩得挺好,一会燕子式,一会穿花绕树式,围着我和小杰一边转一边咯咯地笑。
小杰玩得比我还好,我一问才知道:袁叔叔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带他们姐弟俩来玩溜冰,而他学得特别快,别看他个子小,年纪不大,溜起来都几乎能赶上他姐姐。
冬阳灿烂,晴空如洗,阳光照在远处冰面上,发出闪闪的金光,让人看着心里头暖洋洋的。
三个人滑了一个多小时,小杰提出他已经觉得累了,于是我对雪萱说:“我也有些累了,去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嗯,那边有个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还有卖吃的。”她指着前头几百米处,然后领着我们一块过去。
离永安桥还有几十米的时候,我忽然远远地看见桥上站着的几个人里,有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一刹那间,心房传来一阵剧烈的颤抖。
阳光下,那个面孔,那个身形,那个表情……
绝对是他!绝对是他!!
我几乎要大声叫喊起来,不顾一切地加速往永安桥方向冲了过去。
我知道那肯定是他!
这四个多月来,我何曾有忘怀过!
纵使他是那么地绝情,断绝了和我们的所有联系!
我只恨不能纵身一跃,飞过这宽广的冰面,立即跳到他的跟前……
那个面孔逐渐清晰,我的眼泪却快要涌出,是料峭的寒风,又或是内心的酸楚。
就在跟他还有二、三十米距离时,那个曾经朝思暮想的身影竟然缓缓地转过身去准备离开。
我又惊又急,连忙对他拼命挥手,正要拉下围巾呼唤他。
“啊!”
身后和侧边突然间传来尖锐的惊呼声,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与旁边在玩背滑的一个年青人撞了个满怀。
顿时两个人都摔出去好几米远。
我顾不得左胳膊处传来的那一阵阵剧痛,连忙爬起来,但急切间根本站不起来。
我再抬头一看:桥上的那个身影已经不知道去哪儿了。
我不死心,连滚带爬地好不容易才站起来,没去理会那个被我撞飞的家伙,再次往永安桥冲去。
“胖子!胖子!陆滔!陆滔!”我一边疯了似的呼喊着,一边冲到桥底,攀着桥边的石级,用尽全身的力气翻了上去,然后咬着牙飞快地从脚上脱下冰鞋,光着脚就跳了过去。
“陆滔!陆滔!”
我漫无目的地往几个方向追赶着,声嘶力竭地呼喊着。
直到我发觉自己的声音已经完全嘶哑时,才知道那最后的一丝希望已然破灭。
毫不理会周围人们惊异无比的目光,颓然无力地一屁股坐倒地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缓缓地回过神来,如行尸走肉般回到永安桥。
雪萱和小杰被我的举动吓坏了,一直在桥下呆呆地等着我。
我没说什么,用歉疚的目光看了看他们姐弟俩……
五十三
或许是刚才溜冰时着凉了,回来的路上一直打着喷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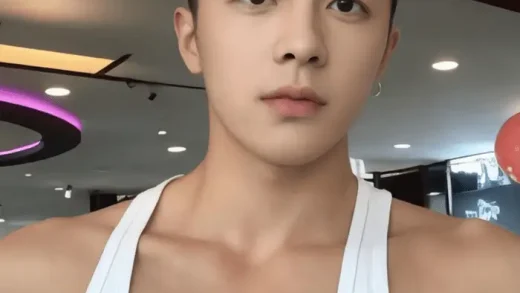
十多年以前的人在写二十多以前的故事
请问遨游四海除了老赵与狗还有没有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