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强一言不发,恭恭敬敬地走上前去,对着爷爷的骸骨“呯呯呯”地用力磕了九个响头。
当他抬起头来时,我分明看到他额头上已是红肿了一块,不禁心中恻然,下意识地看向胖子,胖子也正看了过来,在他的双眼中,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同样的哀伤……
待志强磕完头,永叔又跪下身子去,把父亲的骸骨一块一块地放进了麻布袋,然后抱了起来,对儿子说:“咱回去吧。”
“永子,你要做什么?”宝田爷爷吃了一惊。
“带他回去。”永叔看了他一眼。
“现在?是不是应该等等其他人?”宝田爷爷皱起了花白的眉毛:“好歹你也得等等村长和老支书他们吧,说不定县里还要下来人呢。”
“谁来我不管,第一,他是我爹!第二,我们家的事与你们无关!”永叔淡淡地说。
宝田爷爷伸手拦住他,有点生气地说:“谁说无关的?跟我就有关系!”
“是吗?以前我们家被打成反革命时,您怎么不站出来说这句话?”永叔的目光变得尖锐而冷酷,直盯着宝田爷爷冷冷地问了一句。
说完,永叔自己抱起父亲的遗骸,在志强的搀扶下,再不理会宝田爷爷和大院中的所有乡亲,两个人一瘸一拐地慢慢走出了大院……
宝田爷爷的脸孔变得煞白,下巴上的胡子直抖,似乎还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嘴巴动了动,但终究没有开口。
***
院子里慢慢地开始有人在窃窃私语,都是在谈论志强家的陈年旧事。
我听了一会,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叹了口气,走到胖子身边,两个人对望了一眼,却是无话可说。
不一会儿,院子里又进来一拨人,是村长和老支书他们,但走在最前边的,是兴子和他搀扶着的秋芸阿婆。
我明白了:当年跟着志强他祖父进了地道的两个民兵中,其中一个的家人早在文革时期就被迫害得死的死,流亡的流亡,到最后连祖坟都没人拜祭,这个秋芸阿婆则是另一个民兵的妻子,也是孤苦零丁一个人生活到现在。刚才发现了三个人的尸骨后,志强便立即回去把自己父亲带了来,而兴子则是去通知秋芸阿婆了。
看着秋芸阿婆表情凄苦却冷漠地被兴子和村长等人搀扶着,在好几具骸骨中翻认自己丈夫的遗骸,我忽然感觉胸口有些东西堵得慌,眼泪似乎要从眼眶中涌出。
被冤枉了这么多年,连她和丈夫唯一的一个儿子都保不住,现在纵使能还她一个烈属的身份又如何?独自一个人孤苦零丁地在村里生活了几十年,这种日子换了谁都不会觉得好受吧……
我忍不住拉起胖子的手,转身离开大院……
直到走出很远,直到看不见大院的灯光,我才放开胖子的手。
宁谧的月光下,两个人静静地走着。
“你怎么了?”胖子柔声问。
我停下步子,他也站住了。我凝视了他一会儿,深深地叹了口气,轻轻摇摇头。
“你是为他们难过吧。”胖子说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笑了笑:“很多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了,我们也都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
“我开头还觉得我们发现这地道入口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但我现在忽然觉得如果我们没找到或许会更好,是吗?”我仰起脸孔,望着天空中那一轮金黄色的明月,心中却涌起了一阵哀伤。
胖子摇摇头,开解我:“那小冬兄妹俩就死定了,另外,志强的爷爷和那两个当年拼死冲进地道追击的民兵只怕永远都没有正名的一天。”
他说的完全在理的,我也知道,只是这时的心乱了,尤其是当我想起永叔那副绝望与哀恸的面容,想起秋芸阿婆那凄凉的晚年,就觉得仿佛是自己欠了他们,欠得太多太多……
这时,胖子牵起了我的手,柔声说:“回去吧,我们俩就中午吃了面条,我现在都饿得前心贴着后背了。”
这句话才说完,他的肚子果然一阵“咕咕”作响。
他不好意思地看着我笑笑,我也忍不住乐了,点点头,两人踏着朦胧的月光往外婆家走去。
二十一
回到外婆家,早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不过外婆他们给我和胖子留了饭菜。
我俩吃饭时,大舅和外婆问起了今天的事,于是我就一边吃饭,一边吱吱唔唔地把今天所碰到的事情都一五一十地跟他们说了。
大舅没说什么,倒是外婆感慨万分,让大舅回头抓两只鸡给永叔和秋芸阿婆家送去。
吃完饭,洗过澡,大舅他们都陆续睡下了,我则搬了张竹躺椅放在院子里,静静地躺在上面,望着天上那金黄色的圆月,耳边是田野间啾唧的虫鸣、呱呱的蛙声,脑子里回忆起永叔的那番话语,回忆起秋芸阿婆凄凉的神态,不知怎么地又联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心里戚然而悲,终于体会到母亲这么多年来的孤苦与艰辛,开始对她中年改嫁这件事有些释然……
“想什么呢?”带着一身肥皂清香的胖子刚洗完澡,穿着件白背心微笑着走到我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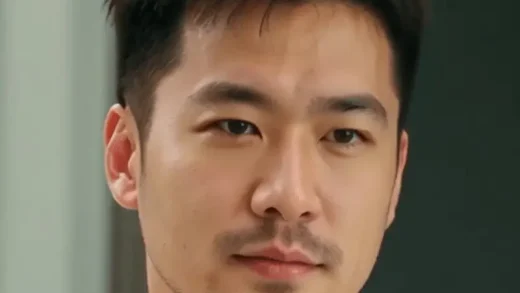


十多年以前的人在写二十多以前的故事
请问遨游四海除了老赵与狗还有没有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