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有三个身穿黑色潜水服的人浮出水面上了小艇,我顿时心中一紧,死死地看着他们模糊的身影,希望能判断出些什么,但很快这三只打捞的小艇开回了岸边,而大坝上的人也陆续地离开了。
等到人都走完之后,王易才轻轻对我说:“你们可以下去了。”我目光呆滞地看了他一眼,慢慢地往大坝走去。
兴子见我脚步有些踉跄,连忙上前一步扶着我。
我看了看他,问了一句:“兴子,你觉得他会没事吗?”兴子没有吱声,只是轻轻叹了口气。
我望着那处高崖,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直发慌。
失事的坡谷距离湖面有二、三十米高差,仅是站在上边往下看便足以让人望而生畏,两天以来又没有任何音询,即便此刻兴子说他会没事也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天,越来越黑了。
站在谷底的湖岸上,那种绝望感越发清晰。
想起和他一块出县城见铁子那次,路上也是几乎堕崖,却想不到前后还不过一个月,便重蹈了覆辙。
我当时为什么没劝他,让他以后开车开慢一点呢?
如果他不喝了酒开车,又或是开慢一点,又怎么会有今天?
还有,他头一天晚上所接的电话到底说了什么?为什么会变得烦躁不安以至深夜未睡?
我的脑袋快要炸开似的发涨,不停地发涨。
手脚也在不停地颤抖着,我想我应该坐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我就这么坐了下来。
可是我为什么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刚才是要做什么吗?
“敦子,”不知道过了多久,大舅在我跟前轻声说:“天已经黑了,我们先回县城住下,明天再过来。”我看着晦暗的湖面,摇摇头:“不,我再等会,再等一会。”“敦子,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可是事情都已经这样了,你坐在这里干等着也不是办法呀。”“舅,您就让我再等他一会吧,”我喃喃地说:“就一会,或许他就上来了……”***
“敦子……”
“总听你说哪天自己不在了我会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我也想问你一句: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的那个人是我,你会怎么做?”“我跟你一起走。”
“敦子,你听好,记住我的话——如果哪天我真的出什么事了,你要好好地活下去,一定不要做什么傻事!你也曾经说过的,你会希望对方好好地活下去,对吧?”“我明白,我记住了。”
他的话轻轻地、很不经意地就在脑海里浮现出来、回响着。
可是我现在不明白了……
难道你当日说这番话为的就是今天?
其实我知道,我一直知道你在担心我。
担心你的父亲像对付阿海一样对付我。
可是我不怕,我说过了:我不怕死,我最害怕的,是和你分开……
你是故意的吧?
是你的父亲终于要对付我了?
我怕什么?
我最怕的,就是现在。
你走了,而我,却还活着……
***
夜深人静,昏黄的台灯前。
我躺在床上,胖子坐在床边脱下军装正准备睡觉。
“胖子,”看着他熊壮的背影,心中温情泛涌,轻轻拥上去搂着他的背膀,在他耳边低声说:“你不离开我的话,你父亲是不是会像对付阿海那样对付我?”胖子不知道我为什么又提起这件事,静静地看着我。
胖子眼眶有些红了,紧紧地抱住我,沉声说:“不!我绝不会让他们动你的,这回就是天王老子也不可以!”言犹在耳,胸口处却痛得有如针刺锤击,而这时胖子的脸正一漾一漾地,映在了眼前的湖面。
“敦子!”
“敦子!你要做什么?”一个惶急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跟着腰部和左边胳膊一紧,被人死死地拉住了。
我缓缓地回过头去:是兴子和大舅。
“做什么?”我看着他们,又看了看湖心,眼神迷乱地指着前边:“我要去看他。”他们大惊失色,连忙把我从水里拽了回来,又将我按坐在湖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敦子……”大舅蹲在我跟前低低地唤了我一声,一边帮我拧干裤脚,一边嗄声安慰我:“敦子,你要是觉得难受,就哭出来吧,哭出来了就会好受些,啊。”“哭?”我呆呆地看着他:“我哭不出来。”
我慢慢地拉起衣服,指着左边胸膛:“舅,我只是这里疼。”大舅张了张口,想要说什么,却背过身子去好一会才转过来,然后看着我,双眼已是红了,点点头:“舅知道,舅知道……”“舅,你怎么啦?你怎么哭了?”我见到泪水从他的眼角滚落,便伸出手去给他擦拭,喃喃地说:“别担心我,我只是想去看他一眼,只是看一眼……”可是忽然间不知怎么地,自己的眼泪也“扑簌”、“扑簌”地落了下来,打在衣服上,一点,一点……
“敦子,你……”兴子又气又急,却又说不出话来,只是跺脚叹气。
一〇五
第二天傍晚,王易自己一个人来了。
他避开了我最后希冀的目光,从车上拿下一只白色纸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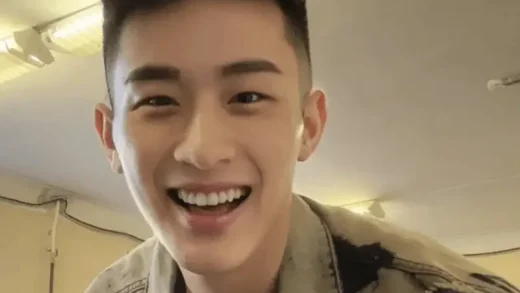

十多年以前的人在写二十多以前的故事
请问遨游四海除了老赵与狗还有没有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