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把房门带好,慢慢地把头上的绷带解了下来。
在他的头皮上有一道好几公分长的伤,伤口已经结了疤,但仔细一看,还是觉得有些狰狞。
想着这样的伤口要是落在自己的脑瓜上,忍不住先打了个寒噤。
正在考虑着要不要让他出去才换时,他已经动手将身上的褂子给脱了下来,露出微腆的肚皮和结实的胸背。
我怔了怔,一时合不拢嘴,不知道说啥好。
他并没看我,很快又利索地把短裤头和内裤也一同脱了。
当我看到他雄伟的男性身体下方那根黑蟒随着他的动作在微微地晃荡时,心里猛地一跳,赶紧背过身去,只觉得自己脸上发烫,脑子里有些反应不过来,呆了呆,才忐忑不安地把身上的湿衣服慢慢脱下来。
上衣换好了,裤子……就当着他的面换?
我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胖子问:“你换好了没有?”我吱吱唔唔地说:“差不多了。”
他没出去,在一边等着。
又过了一会,他奇怪地问:“换好了没有?”
“快了……”我头有点大。手里拿着短裤,眼睛却看看桌子,看看椅子,就是没有动。
换不换呢?不换的话裤子湿漉漉的贴在身上很难受,换的话就得让他出去才行……
“你是不是脚疼不方便?”他又等了我一会,见我没动,就走了过来问。
“不是,不是。”我连忙向他摆手,对他说:“你……你背过身去一小会,当着你面我不好意思扒裤子。”他愣了愣,随即大笑,最终还是转过身去。
趁着这个当儿,我飞快地脱下裤子扔了一边,又飞快地套上干净的裤子。
说起来还真有点丢人,这估计是我有生以来换衣服换得最快的一次了,如果有这种比赛,我想我保准能拿个第一!
我对他说:“行了,换好了。”
胖子慢慢地转过身来,看着我眯眯眼地笑着。
我知道他在笑啥,脸上又热了一把:“谁像你脸皮这么厚呀?当着我的面就直接扒裤子,都让我看光了!”他呵呵呵地笑:“你看就看呗,我怕啥呀。”
我按着椅背要站起来,他赶紧伸手过来扶我。
他的手宽实有力而且温暖,给人一种很踏实的安全感。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想起刚才他换衣服的那一幕,有些好笑。
当我和胖子都换过衣服后,巧儿和雪兰姐妹俩已经把药酒拿出来了。
外婆先给他看了头上的伤,告诉他已经不需要包扎了,他依旧只是对外婆笑笑。我瞄了他一眼,他现在的样子比先前显得好看很多,于是目光不由自主地又在他身上多停留了一小会。
姨妈接过药酒,准备捋起袖子要给我涂抹。
这时胖子说:“大姐,让我来帮他上药吧。”
姨妈看了看他,笑着点点头:“轻着点,刚扭伤的地方不能使太重的手劲。”胖子笑了笑表示明白,然后从姨妈手里接过药瓶,帮我轻轻地涂抹着。
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坐在脚边认认真真地帮我上药,我心里边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
下午哪都去不了了,只好乖乖地呆在家中看看书。
晚饭前大舅和三舅他们都回来了,一大家子人老老少少的围在一块吃饭显得非常热闹。
至于我们捉回来的那条锦蛇,则被大舅拿到后院炖了做菜。
看着这碟炝蛇丝,我有些郁闷:哎,算起来还是得不偿失啊,捡的野鸭蛋都给打的差不多,唯一的收获就是这碟菜了。
大舅拿出了一瓶白酒,让雪兰洗了杯子,分别给几个大男人都斟上,还特地给姨妈也倒了半杯。
姨妈笑着推说不喝,大舅不答应了。因为知道她其实酒量不小,再说她不常过来,难得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便坚持要她也喝上一杯。
小雄和小斌也吵着说要喝,三舅妈拦着不让。
雪英在边上对他俩撇撇嘴说:“哼!小屁孩,也想学大人喝酒?你俩应该去喝奶才对。”大伙儿好一顿笑。
大舅哈哈大笑着给他们小哥俩各倒了一点。
两个小家伙抢着杯子各喝了一口,小斌马上吐了出来,一边“呸呸呸”地吐,一边嚷:“好难喝。”小雄则是咂咂嘴,皱皱眉头,把杯子放回来。
大舅笑着问小雄:“好不好喝呀?”
小雄看了看大舅,想了想,摇摇脑袋说:“没有汽水好喝。”
这下把我们都逗乐了。
我偷偷瞄了一眼胖子,胖子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几个孩子,神态温和憨厚。
席间,大舅频频举杯,他酒量很好,几杯下肚,跟喝水似的。姨妈的酒量也不错,开头只是说喝半杯,后边喝开了,倒过来跟大舅一块变成劝酒的人。
胖子因为头上有伤,所以只喝了一点外婆就不让他喝了。
我酒量顶多也就三四两的样子,喝了半杯之后推说脚痛不能喝,但大舅不肯,说我脚上的瘀血喝点酒更容易去瘀散肿。我本想向外婆求援,结果外婆只是在一边笑,也不帮我挡酒。
我又看了看胖子,见他也在笑眯眯地看我,只好硬着头皮跟他们继续喝,一来二去,最后把三舅和我给灌倒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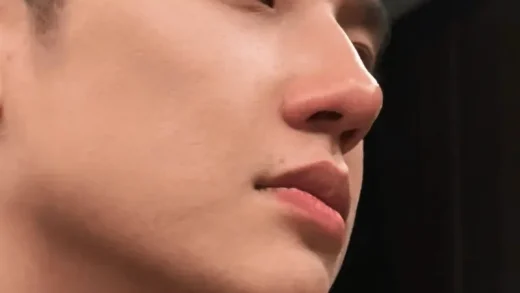


十多年以前的人在写二十多以前的故事
请问遨游四海除了老赵与狗还有没有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