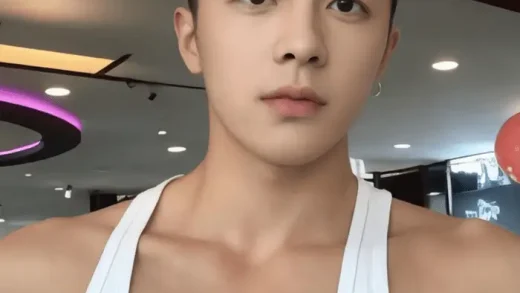柱子冷哼了一声,侧身向着墙。他的确是这样考虑的。上次王芃泽走的时候也说这个周末不再过来了。早上天未亮时他曾经想过回家把沙老师的事说给王芃泽听,反复想过之后觉得还是算了吧,王芃泽是人不是神,能有什么办法?只会徒增烦恼与担心。
周秉昆建议道:“不如我们去江边玩吧?”
这一天天色阴沉,柱子看了看窗外,说:“看样子今天会下雨,长江会涨水吧?有危险。”
“南京下雨,长江涨不了什么水。”周秉昆道。“算了,你不想去就不去了。”
过了一会儿,周秉昆又说:“王玉柱,我想到一件事情,你一定会去做。”
然后把胖胖的脸凑近柱子的耳边,悄悄地说:“你该把红花油还给沙老师了。”
柱子伸手到枕边摸到那瓶红花油,举到眼前翻来覆去地看,窗外阴沉的天色映进来黯淡的光,让这个古色古香的瓷瓶越发显出一种神秘的气息。
走出宿舍楼的时候柱子还有些犹豫不决,对周秉昆说:“其实可以下周沙老师来上美术课的时候,我趁课间还给他。”
周秉昆说:“你那样做,班里的同学都会看到,有几个人可是一直在等机会报复你呢。”
学校里的单身宿舍已经很破旧了,楼梯是木头做的,走上去颤巍巍的,有几处破成了洞,可以把楼梯下边的那一层看得清清楚楚。
两人原以为这单身宿舍里一定很多老师,于是带着学生对老师的固有的胆怯,放轻了脚步走进去,看到从一楼到三楼都是安安静静的,并没有多少人在这栋楼里住。三楼更是静得没有一点儿声音,几只麻雀在走廊上觅食,扑棱一声飞出了窗口。
周秉昆指着走廊最里边的一个门,对柱子小声说:“看到没有,那个屋子就是,你跑得快,把红花油放到他的门口就赶紧跑回来。”
“啊。”柱子惊讶道,“不跟沙老师说一声么?”
“你还想跟他说话呀。”周秉昆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句之后,话语又迟疑起来,觉得这样做的确不好,“可是沙老师人很怪,从来不和人说话的,你要是想打招呼的话,就敲门吧。我在这儿等着你。”
“你不一起去么?”
“我不去了,又不是我来还红花油。”
柱子往前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周秉昆躲在楼梯口,探出了半个脑袋望着他。
走近沙老师的房间的时候,可以听到从里面传来收音机的声音,咿咿呀呀地唱着戏。柱子心里紧张,其实也很怕直接面对沙老师,他决定敲门之后数三下,如果没人开门,就把红花油放在门口,以后见到沙老师的时候可以解释说敲门了,但是你在放收音机,没有听到。
他轻轻地敲响了门,屋子里收音机的声音依然在响,唱的是昆曲,突然结束了,电台主持人的声音在响:“刚刚播放的选段是……”然后有人转台了,收音机呲呲地响,把这个寂寥的长日渲染得更加漫长。
没有人过来开门,柱子在心里默数:一、二、三。然后松了口气,立即放下那个小瓷瓶,蹑手蹑脚地往回走,走了一半的路时,突然“吱呀”一声,有人开了门。柱子吓了一跳,匆忙转过身,直直地站立着。
的确是沙老师房间的门开了,有人蹲下去,花白的头发露在门外,伸手出来捡起了红花油,然后站起,整个人走了出来。沙老师穿着背心长裤和凉鞋,一下子还习惯不了走廊的昏暗,眯着眼望了一会儿。
柱子急忙说:“沙老师,是我。”
“你是王玉柱?”沙老师淡淡地笑了一下,在黯淡的光线里几乎看不出来,“这红花油,其实你不用还。”
柱子知道周秉昆在背后盯着看,有些紧张地站着,不知该说什么,沙老师说:“进来坐一下吧。”
“不坐了。”柱子指指窗口道,“要下雨了,我得赶快回宿舍。”
话音刚落,天空就响起了一声惊雷。
“我给你拿把伞吧。”沙老师说着就要进屋去拿。
柱子急忙推辞道:“不用不用,还没下呢。宿舍很近,我很快就跑回去了。”
沙老师不再勉强,站在门口目送着柱子转过身去,在楼梯口消失。
4
寝室里渐渐开始讨论女生和性,这是男生宿舍里永远的话题,刚开始大家都还拘谨,带着自初中而来的努力学习的习惯,一边讨论女生一边讨论功课,后来功课便被远远地抛开了。中专与初中不同,不再有升学的压力,大家又都是处于青春期,性话题于是成为了男生最大的乐趣,寝室里那六个或戴着眼睛,或读书读得斯斯文文的男生,似乎突然间发现了自己精神中狂放不羁的一面,每晚熄灯前必会兴致勃勃地释放自己心中的野性,两眼放光地狂聊狂侃。
有天晚上周秉昆不想听那些猥亵的笑话,对六个人抗议道:“你们以前嫌我吵闹,现在却吵闹得比我还厉害,大家要在一起住三年,你们不会是三年都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