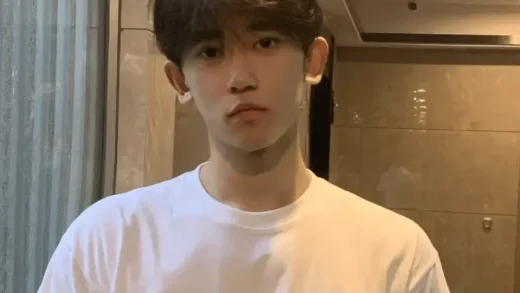伤口慢慢愈合时,可能是痒,还不敢乱挠,我会给他抹点痱子粉,前前后后的伤口抹完,我会问他,那个地方要抹点吗?
他就笑笑。
有一次,他痒得受不了,大半夜把我摇醒,要我用湿毛巾帮他擦身子。
从上到下擦完一遍后,我问他,还痒吗?
他说不痒了。
我说,那个地方不痒?
他又只是笑笑。
他的淡然刺激了我,我又问,要擦吗?
他却反问我,你是想擦还是不想擦?
我颤微微说,我可以说想吗。
他还是笑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得意还顽皮地说,那你就擦。
我谨慎地抹着那根洋溢着生命活力的东西,那种真实的触感一瞬间击中了我原本就脆弱的神经,擦着擦着,他没硬我倒硬了。
见我躬着腰慢慢退回卫生间,他却笑得双手不停捶床。
我心理不平衡,帮他清洗脸上慢慢愈合的伤口时,取笑他:“破相了,娶不到媳妇了。”
可能是痛,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娶不到媳妇和你过。
我说,你还真赖上我啦,谁要你跑的。我嘴上这么说,心却想,怎么不摔严重一点,彻底破相真娶不到媳妇才好呢。
“那警察太烦人了,一个劲吹哨子,我不跑都不行。”他想起了那个警察。
我说:“你傻啊,人重要还是电动车重要。”
他就强词夺理:“那不你送的嘛。”
他还会要我给他按摩。
吃过早饭后,他趴在窗台下的那张躺椅上晒太阳,他看不惯我撇下他一个人玩电脑,要我给他按摩,他后背有伤,我也不能太使劲,就在他的大腿上揉来揉去,他的腿毛很重,摸着很舒服。
他舒服地闭上了眼睛。
我问好了吗?他说,再按一会。我又问好了吗?他还是说,再按一会。我再问,他就说,抠门劲儿的,多按按会掉块肉啊。我就扯他大腿上的毛。他痛得大叫,说,你扯我腿毛干什么。我说,你腿毛那么多,扯几根也没事。他就屁股一拱,说,这点毛算什么,我下面更多。
可能知道他身体有伤,我不会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他时不时会肆无忌惮抛出一两句诱惑性的语言,还露出坏坏的笑,那种不怀好意的坏笑像某种神秘的蛊,我不知不觉就中了这种蛊。这种感觉像冲破决堤的暗涌,有好几次我气得真想脱光自己,咬咬牙压上去算了,但一看到他遍体班驳的外伤,又不忍心下这个手。
那时,天很热,他不能洗澡,后背出了不少红色的小斑痘。晚上睡觉,他会要我帮他挠。挠轻了,他会说你没吃饭吗,挠重了,他又说,你手不会轻点。我干脆用手掌轻轻地摩挲,后来他竟成了习惯,每天晚上必须给他摩挲一会儿才能睡着,我手一停,他就会说,你怎么又停了。
我说我还能给你挠一晚上啊。
他就说,你要受伤了我就帮你挠一晚上。
我说,挠出火来了怎么办?
什么火?他一楞。
我色色地说,还能什么火,欲火。
他突然就笑:“那我没办法,你自己蹭墙去。”
有一次,我挠着挠着受不了,下床去阳台抽烟。他见我半天不回来,跑过来似笑非笑问,怎么,你火出来了?
我气得把烟头掐灭,说,你再说,信不信一会儿我办了你。
他吓得吐了吐舌头,行了,不刺激你了。
有时,中午,我们躺在床上,我用扇子给他的身子扇风,扇着扇着,他就睡过去了。我在旁边看着他睡,他熟睡的样子很安详,每一次呼吸和每一次胸口起伏都充满节奏感。
帮他洗衣服时,他也会用扇子给我扇风,哼着小曲。洗完衣服,他搂搂我的肩膀,说,等我的伤好了,我给你洗。
伤口慢慢愈合后,他就上班了,他下班回来我会习惯性地说:“来,把衣服裤子脱了。”
“干嘛?“他问。
“帮你擦身子啊。”
“不用,已经好差不多了,我自己可以擦。”
“好了就不要我了?”
“行了,你想看我身子就直说,我现在就脱给你看。”他直直看着我,眼神好像探照灯,一下照出了我内心的龌龊。
“去死,我又不是没见过。”我慌乱地垂下眼帘。
“……”
他还经常穿一条大裤衩在我面前晃来晃去,那条大裤衩没有松紧,用一条长长的带子系着,有一次,我突然拉了一下那条带子的结,他的裤衩差点掉下来。
“想看直说,我脱你看就是了。”他还是那句话。
“你脱呀。”这回我没说又不是没见过,而是用冷静的表情直直地盯着他。
他和我对视几秒,微微一笑,话锋一转:“行了,该把电脑让给我了。”
由于网店的生意也不咋地,我就听了我妈的劝,暑假去了驾校学车。我妈是希望我学会开车后,以后能陪她去沈阳上货。
马小强会骑电动车送我过去。
我见他对学车非常感兴趣,就用他的身份证偷偷给他报了名。
马小强不肯去,要我把钱退了。我假装去学校问,骗他说,不好使,不给退。马小强要给我算钱,还说等发工资了一点一点还。我说,算那么清楚干什么,你不是都说要和我过吗。马小强就撇了撇嘴:“切,你还真以为我娶不到媳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