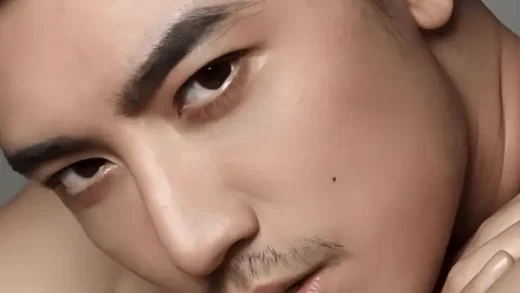我去爬了慈航寺后面那座山,走累了,停下来,在一棵树下,站住。
那上面,多年前,我们彼此刻下自己的名字。
我抚摸着那棵早没了痕迹的树,眼泪一滴一滴的掉下来。
一切的悲欢离合和生死歌泣,虽然反复失去的痛苦经过时间打磨,已不像十五六岁时那样五脏俱焚,但我扶着树,还是哭出了声。
我以为自己很坚强,有放弃一切的勇气,结果发现自己其实是脆弱的。
下了山,我去了那家回族面馆吃面,我想起马小强的母亲把她面条上薄薄的牛肉片夹到我碗里,说,吃,快吃,怎么不吃啊?
眼泪在眶里打转。
我还去了千金和我的老母校,冷清萧瑟,面貌全非,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样。
我又想起电影里,吴倩莲问黎明:回不去了。我们回不去了。是吗?
是啊,回不去了,一切都回不去了。
我甚至还去了马小强和海娜新房的小区,我呆呆地坐在小区一个角落的石凳上,呆呆望着那天蓝色的窗帘。
外面阳光很好,却照不到我的世界。
我在思考,我为什么会爱上一个同性?
两个明明很相爱的同性为什么就不能在一起?
我们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们反动了吗?
我们违法了吗?
我们违反人类准则了吗?
想想我们这种人,怀着一颗伤残的心,却还要在大家面前活出正常人的样子,是多么的艰辛和不易啊!
直到夕阳西下、夜幕降临,天蓝色的窗帘突然亮出一道光,我才悲戚戚地往回走。
我突然想起那首诗:
月儿弯弯照九州,
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妻共帐罗,
几家飘零在外头。
华灯初上,该是到了他们共帐罗的时候了,我却还在外头飘零。
你说他也会拉上窗帘,扑到她身上,兴奋地说,咱俩该入洞房了吗?我戚戚地想。
离开小区,我在外面飘荡到很晚才回去。
人烟稀少的街道,夜凉如水,看着一盏灯熄了,又一盏灯也熄了,我眼前的景象变得黑暗模糊起来。
离开本溪的前一天我没出门,安安静静呆在家,对未来的恐惧犹如小虫肆啮我的心,我仿佛看到了自己人生的终点。
我的奶奶敏锐捕捉到了我内心的变化。
我和我奶奶相差近六十岁,许是年龄差距的缘故,记忆中,我们从来没有相互倾诉过。
在她眼里,我太小,在我眼里,她太老,彼此都不是对方合适的倾诉对象。
但那晚她说了很多,问我最近马小强怎么不过来。还给我说了很多有关她和爷爷的事情,我只是静静地听着。
当她说出,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经历这样或那样苦难,我们要善待自己,善待生活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热泪顺眶而出。
告别本溪湖,告别慈航寺,告别那棵曾经刻着我俩名字的树,告别了千金还有我的老母校,告别了一些人,还有这座城市……
列车上,传来梁静茹的声音:终于作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去……
突然,我泪流满面。
我去了银川。
我很喜欢银川这个城市,他就像马小强,老实、安宁,踏实、沉默。
找到了我爷爷奶奶曾经去过的一个清真寺,参加了一场宗教活动。
宗教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
这种神秘就像一种暗能量,让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根本没有勇气去面对。
我抬头看着又高又远的蓝天,心中突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圜寂和虚幻。
活动进行到一半,我便逃也似得离开了。
我去了深圳参加吕辉的婚礼。
我私下问吕辉,那次万丽丽结婚,我们出去唱歌,你说的那些是不是真的。
他说,你那两年没收到我给你送的生日礼物吗。
我说,什么生日礼物?
他说,一盒心型巧克力啊。
我一楞,靠,我还一直以为那是马小强送的呢。
我和他讲了我跟马小强之间的事情,听到他一声叹息,我忍不住眼圈一红。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上次我就想劝你,别太认真,你们长久不了,看你们那腻味劲儿,我就忍着没说。”
我哽咽着说,没事,我就是突然间好难受。
当我来到最后一站——广州,回到我亲生奶奶身边时,我以为,一切会重新开始。
但我错了,我还是我,所有的记忆都在,所有的痛苦和思念都在,而且被放大了很多倍。
每天晚上,我看着抽屉角落那张自离开就没打开的电话卡,我就会想马小强的各种表情,比如歪着脑袋看我,冲我恨恨地坏笑,我欺负他时咬牙切齿的神态和徉装嗔怒的小表情,醒来时眼角居然还有泪。
在广州的每一天,我感到异常孤独,我甚至在想,我最后的结局一定是流落街头,客死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