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雪粒簌簌地疾速降落着,抬眼看天,雪粒子-射进了我的眼。揉揉眼,伸伸粉红的舌头舔舔脸,我要去看我的老韩在干什么,我一天不在,他吃了么,喝了么,睡了么,千万别饿了他,冻了他。
纵身一跃,已到高墙之外。我不再回头,纵身前行。
我很讶异自己竟然这样能奔善跑。我念《四张机》的大水库和杨树林被我抛在身后,再纵,再飞跃,华县县城,渭南,临潼,灞桥统统被我抛在身后。
快到玉祥门了。我不由得停下来。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走不动了。
护城河在暗暗流动着,除了河边的薄冰上敷着一层雪外,河水在夜色里看起来竟然是黑色的。难道我是为这个停下的吗?我想不是。
街灯整齐地站立着。我抬头,雪粒子在灯光下不再那么晶莹洁白,像雨一样落下来,落到地上近处色淡远处色深。我想我不是来看这个的。
可是我为什么走到这里就走不动了呢?
我在路上很茫然。
忽然两辆小轿车朝我迎面冲过来,我还来不及看清车牌号,他们已经无睹我存在似的从我身上碾过。更奇怪了,我竟然没有被碾成相片也没有被撞开。我还直直地站在原处。
我回头看自己的尾巴,我的尾巴还光鲜可爱。
可是,我闻到了一个人的味道。
我知道,我之所以走不动,是因为,我还应该去看我的那位大哥。
☆、261
在这雪夜的梦里,我竟然变成了一只白狐!
田真真无数次地骂过我是一只狐狸精,是一只专门迷惑男人的妖精。
为了这一句话,田真真遭遇到了可能是有生以来的头一次羞辱,并为此食不甘味夜不成眠。
我不知道就在这个夜晚,为什么我连自己做梦,都变成了一条被人诅咒的狐狸!
我不明白这是还原了我本来的面目,抑或是来自对自己是个同志的罪恶感,还是对田真真的愧疚感,还是确确实实来自内心深处一直深深隐藏的自卑?
难道说,我真的在众洌呐略谕救χ幸彩歉鲆炖啵?br>可是,飘雪的夜晚,我除了在路灯下做了片刻的踌躇,再纵身一跃,朝我玉祥门的家里奔去。
不用敲门,我已到了屋内。
橘黄色温暖的灯光下,老左懒懒地半躺在软和的丝棉枕头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在读。我感到奇怪,老左行伍出身,哪里曾认真地这样读书过?
“哥,你看啥书呢?”
老左甚至没有瞟我一眼,欠了欠身,翻了一下书页,继续认真地看。
我两只脚搭上床沿,鼻子顶了顶老左手上的书。
一看书名,我乐了,原来老左在看一本数学练习册,这分明是他女儿的课后习题嘛。
“别看了,早些睡吧。我都看过了,这孩子,做的很认真。”
跟着轻轻地磕门声,门口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田真真!
田真真在我的屋子里,我感到非常惊讶。可是片刻的惊讶后,我又感到万分欣喜,他们复婚了!这不就是我一直想看到的景况吗?
老左从书上抬起头来,笑了笑:“孩子睡了吗?”
“睡了!你别操心了,早点睡,明天还要上班呢。”田真真说着,上了床,掀开被子,紧贴在老左身边躺下来。
老左放下书,伸出胳膊揽住田真真的肩膀,脸紧紧贴在散发着淡淡香水味的田真真的脸上:“老婆……”
田真真转过脸,努起双唇,“啵”地在老左脸上亲了一口,伸手在老左的身上摩挲起来。
他们亲热的时候,我就站在他们床边,他们却视我不见!
我不能再呆下去了,准备扭头离开。
“今天孩子他们班又调座位了。原来跟小辉同桌的,现在却跟一个叫什么洪小军的一张桌子。”
田真真轻声说。
“哦!”老左应了一声,越来越重的呼吸声使他后面的话有点含混,“跟谁坐一桌都一样,问题是咱们孩子自律性好,这还不是从你那里遗传的?”
田真真迟疑着说:“不知道为什么,小辉和洪小军这两个名字,我老是觉得跟我们有点儿什么关联,一想到这两个名字,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憋闷。”
老左紧紧地搂住她:“别瞎想了,不就是个人名儿么?就跟鸡呀狗呀老虎狮子狐狸一样,只是个名字……”
我以为在听到田真真提到“小辉”和“洪小军”这两个跟我息息相关的名字的时候,老左会有些我期望的一些反映,可是,听这话,老左根本就对这两个名字漠不关心,我不由得一阵心酸。
难道说是田真真给老左喝了什么迷魂汤?还是老左根本就不曾与我认识过?可是,我忽然心里很坦然了,既然老左跟田真真已经和好如初,既然他们已经不再能记起我,甚或更记不起我曾带给他们的伤害,我何必还要赖在这里呢?
雪依然在下,我恹恹地来到了雅馨园。
我跨进门,屋子里乌烟瘴气,呛人的烟味熏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揉揉眼,我发现屋里满是人。一圈儿沙发上坐满了人不算,连我的卧室里也围满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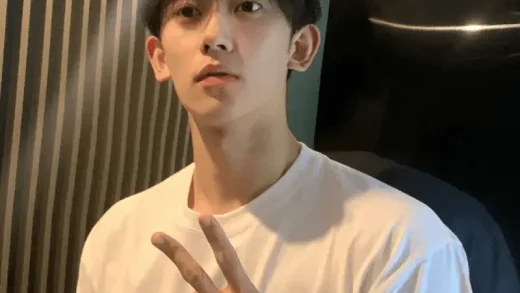


看过很多小说,不得不说这本写的挺失败的,人物塑造的很失败
太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