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巾上散发着一种诡异的浓浓的栀子花香,不等我再呼吸,一种从未有过的困意铺天盖地而来,身下逼人的潮寒,远处阑珊的灯火,广场上的几辆车子,似乎被谁用法力巨大的钵盂尽数收了去一样,连琐碎的一些声响,也都离我越来越远。
也不知过了多久,疼痛,在我慢慢有了意识的时候阵阵袭来。掀开沉重的眼皮,我这才发现,我正侧卧在一张坚硬的木板床上。两只脚,两只手,分别一圈圈缠上了工业用胶带纸,我抿一抿嘴唇,发现我的嘴巴也被人贴上了。
四处打量,这是一间不到十平米的房子,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透气孔。天花板上吊着一只并不怎么亮的白炽灯,床对面摆着两张陈旧的写字桌,桌面上堆着一只装苹果的空纸箱,箱子里塞满绿色的空啤酒瓶,箱子旁边放着一副碗筷。地上有一只半旧的绿色塑料盆,半盆污水和地面一个颜色,盆沿上搭着一块皱巴巴分不清颜色的毛巾。身下的被褥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霉味和酸酸的臭汗味。
这是哪儿?我昏睡了多久?我无法找到答案。
屋子里没有一个人,墙上也没有钟表。我洗得有些发白的牛仔裤上,膝盖处已经磨烂,线头绽开来,露出里面的羊绒裤上有渗出来的血迹。蓝灰色的高帮休闲鞋上也粘着斑斑血迹,我不知道这些血从何而来。鼻子有些难受,艰难地抬起手臂蹭了蹭,袖子上竟然也粘了几片血痂,低头看,低头看,手掌上,也是血痕一片。
门关着,外面有几个人在说话,我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也分辨不出他们的口音。
身下很酸麻,我努力地扭动身体想坐正,“咚”的一声,一块报纸包着的可能是当作枕头的砖头被我蹭落到了地上。
响动过后,外面的说话声停了下来。
“狗日的醒来了!”
这是地地道道的关中音律,而且这声音好像在哪儿听过,难道说,我回西安了?
随着这粗粗的一声叱骂在门口响起,一阵脚步声纷沓而来,门开了,随着一股冷风,进来了几个人。
最前面的人我是认得的,是那个被二哥曾经一顿猛揍的张二狗,刚才那骂声也分明是他的。张二狗后面的人是一个约么三十岁穿黑夹克的男子,再后面跟着的,正是老骆。
见我睁开眼在床上蜷缩着朝他们看,张二狗三两步冲上来,抬起腿,狠狠的一脚朝我踹来,因为床高,他这一脚正好踹在我的脚踝上。
我不由得回缩了一下腿。强忍着痛,没吭声。此时在看见张二狗,我忽然有一种不祥之感。贼,都是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张二狗和老骆他们丝毫不顾忌我认出他们,看来,我这次真是凶多吉少了。
“啪”,一记重重的耳光,摔在了我脸上。腮帮里一股咸咸的味道随着唾液涌上来,我本能地努努嘴。
“刺啦”一声,我嘴巴上的胶带纸被他一把撕掉。
“你狗日的也有今天!妈的逼,你有本事的话,叫你洪家弟兄再来打我啊,有本事的话,把那个沟子客韩军也叫来,让他再来拾掇我啊!”
张二狗似乎还不解恨,随手又掏出一个东西重重地砸在我脸上。那东西弹了一下落到我身旁的床上,竟然是我的手机。
“噗——”我一张嘴,一股血唾沫直直地吐在他脸上。
今天落在这帮人手里,想全身而退的希望很渺茫。我干脆豁出去了,再怎么说,我还不至于怕他张二狗这样的滚刀肉。
张二狗抹了一把脸,看见血,更是急红了眼,上来抓住我的衣领,啪啪又是两个耳光。
身后那个黑夹克男人一把揪住了他,笑着说,“算了,二狗哥你也歇歇,你还真想现在打死他啊?他可比你我都值钱啊!”
张二狗骂骂咧咧一边去了。
老骆笑了一下,上前道,“小辉,你知道不,这儿是啥地方?”
我瞅他一眼,脸转到一边不再看他,也不言语。
“这是一个为备战准备的能当容纳几万人的地下防空洞,上面可就是大唐不夜城了。不过,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人能听见,这儿可再没有其他人了。你要是乖乖地合作,兴许还能活着见到你哥老韩,再要是消极对抗,你的小命就不好说了。我明明白白告诉你,就不怕你有机会逃出去。”
我冷笑一声。
“目下这社会,啥,最能靠得住?你也不看看,给你大哥十万块钱,他就能乐得屁颠屁颠的,问啥说啥,难道他还顾念你们是一奶同胞的弟兄吗?象他才是聪明人呢,谁会跟钱过不去呢?老韩跟文清争啥呢?说白了,还不是为了争钱,倒不是为了村长这个虚名!”
老骆从我身边拿起电话,在上边摁了一下免提,再拨出去一个号码,他把拨通的电话放到我嘴边,“来,跟韩军说两句话!”
不晓得现在是什么时分,在这昏暗的停车场的小房间里,看不出时间。墙上的风口处,黑魆魆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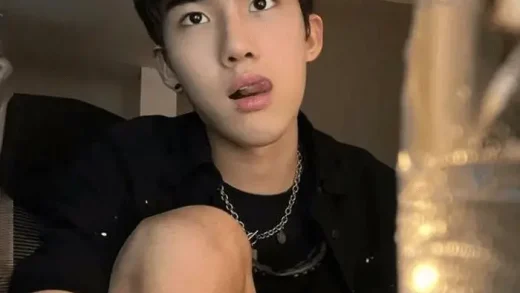
看过很多小说,不得不说这本写的挺失败的,人物塑造的很失败
太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