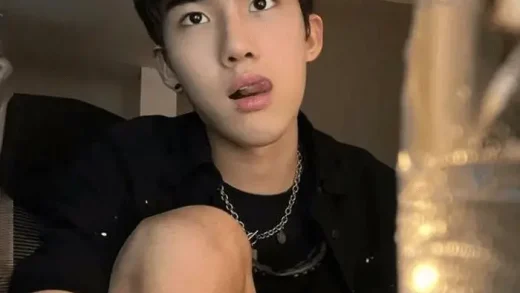我儿子头上的伤已经缝合,正输着血,已经没事了。我老婆哭着诉说他怎么找不到我,我手机又关的,所以她只好打电话给雷米,雷米也肯定是到处找不到我才会怀疑我在那个酒吧的。雷米看过我儿子后,陪我们坐了一会就说:“现在没事了,我先回去吧。”我才开始渐渐恢复思维起身送他。他一言不发地起动车子,我说: “我们去吃点夜宵吧?”他头也不抬地说:“吃不下。”我又说:“那去喝点什么?”他抬头看着我说:“你还是留下来陪陪他们吧。”说完车子就去了,我仍然愣在那里好一阵。
雷米的冷静让我产生幻想:他是不是真的不太在乎我做这事?但我马上打破了这个幻觉,他对爱要求那么完美,怎么可能容得下我们之间发生这种事?说不定这次我死定了。他如果发泄一通还不可怕,他这种冷静往往预示着一切都无可挽回。坐在我老婆身边的两个多小时,我的心都七上八下的,猜测着可能会发生的事,我觉得我必须现在就去看他,否则我要窒息了。娜姆一叫我回家休息时,我马上打车去了新居。
灯光还亮着,他在健身房打着拳击,“硼,硼,”每一拳都像是打在我心上。他已浑身湿透像从水中上来一样,短裤的腰上也湿了一大圈。见我来他也不停下,打得更用劲,我等了他半个小时,他仍不停,我想今晚他会这么一直打下去直到把自己累瘫。就走过去按住他的手说:“该休息了。”他看看我,筋疲力尽地脱下拳击套进浴室去了。从浴室出来他拿了一瓶矿泉水喝着,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像看一外星人。
我搜肠刮肚地找词儿开头说话,却怎么也找不到可以说的。最后他问:“你对我的激素用完了?”我说:“没有。”
他的脸通红,神情几近衰竭,目光无神地看着我说:“你应该早点儿告诉我,你们都只是玩玩儿,不认真的。这种游戏规则谁都懂。”我说:“不,阿雷,我从没和你玩什么游戏。认真不认真那就要看对谁了。”他问:“那你对谁认真?”我不敢再实话实说,怕更激怒他。他喝完了水,玩弄着手中的瓶子说:“你说得对,我就爱把事情想得太完美,一厢情愿地愚弄自己。”我忙说:“不是这样!阿雷,你听我解释,我…..”他打断我说:“解释什么?那是我的幻觉对吗?”
我又觉得真的没什么好解释的,事已如此,说什么都没用了。见我没话可说,他更绝望,站起身说:“我要睡了。”
他缓缓起身的动作扯着我的心在痛,仿复他的四肢和我的心是用钱拴在一起的,他再动一动我的心就要撕出血来了…………
我几乎是想哭地从后面抱住他,想让这讨厌的事立刻结束,想让他看到我此刻是多么真城地懊悔,想让他觉得我多么可怜:“阿雷,我爱你,你原谅我吧,我永远不会再干这种蠢事了。”他推开我说:“我很累,没有精神再和你纠缠。你爱干么干你的去,只是不要再说你爱我之类的话了,我现在听了就恶心。”
他想强忍住溋滿眼眶的泪水,但泪水却不争气地跌落下来。这柔软的泪水却有千斤的重量,砸在我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牵着我的泪涌出来,我痛得紧紧抱住他,他发怒了,吼道:“滚开!”他摔开我进了卧室把门从里面锁上了。他恨我看到了他的泪水。
世界又是一片沉静!所有的家俱都鬼鬼祟祟交头接耳地讪笑着我——活该!
我怕他半夜出走消失几个月不见我,就不敢去睡,只好躺在客厅沙发上听着他的动静。他一直没有出来。我就在沙发上睡了一夜,其实是四个小时。
天一亮他就出来了,光着脚到各个房间找东西,我看着他收拾电脑室的软件、文件、书和他的拳击套就知道大事不妙了,忙上去拉他说:“阿雷你别这样,我的错是不可饶恕,但你也不该这么就走啊,咱俩还不至于就到了这一步。”
他一拳打在我腹上,抬起我的下巴说:“我现在就搬走,这里留给你作鸭窝,以后你就不必在外面做了。”他把东西放在车上,又回来拉海伦,海伦愉快地跳上了车。我追过去拉开车门,他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推开我说:“滚开!别以为谁离不开谁,我饶你不死算便宜你了,你以后别再来招惹我!”他关上车门就开车走了。
我自作自受地陷入太平洋底。
我在门口站了好一会,恼怒地想:我怎么就这么倒霉?第一次出轨就被他发现,他一定认为我一直在这么干,我现在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他再也不会相信我了,他又是这么认真的人,跟本不可能原谅我,这一走他还会回来吗?是什么魔鬼在捉弄我?我一抬头看见我们的邻居那对俄罗斯夫妇在窗口偷窥着我,就冲他们大骂: “看什么看!要看出来看!克格勃贼性不改!”他们立刻在窗口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