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吗”
他摇摇头。我看不到他的脸。我翻身从枕边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润滑剂抹了很多在自己的荫经上,再帮他往肛门里抹,他的肌肉稍稍抖了一下。
“有点凉”我说的时候他仍是背冲着我。
我示意让他上面的腿抬起来一点。我的荫经慢慢地试着往里插。这个姿势很难的,可他一直那样躺着,我也不好强求。我的“家伙”刚进了个头,就一下子歪了出来。电视里那个年轻一些的小伙子已经被插的浪叫了。蓝宇转过脸,紧张中带着兴奋。我让他两腿分开跪在床边,肩膀压得很低,这是最容易干的角度,特别是第一次,可看起来有点下贱。我的荫经开始慢慢往里送,他的手紧紧抓住被单,没有一点声音。当我全根没入的时候,他手抓的更紧,发出一声几乎听不到的呻吟。太棒了这不仅仅是性器官的反应,他那种非常痛苦的忍耐让我感动,近乎疯狂。我想尽量缓慢的菗揷,以便减轻他第一次的疼痛。可我的意识早已混乱,我情不自禁的叫着“啊我天天想你,想死我了,想死我了太棒了真太他妈的”我顾不得许多,拼命地菗揷,虽然有足够的润滑剂,还是很紧。我的一只手下意识地摸到他的“家伙”,帮他手淫。
“嗯”他又发出那种压抑的兴奋声。我突然觉得我的手湿滑一片,他的机巴猛烈地抖动,我的天他居然在我之前设精了。我也随之一泄如柱。
那天我们做完爱都没有洗澡,任其肮脏着。我没有象以往,倒头便睡,而是象对女孩儿那样搂着他爱抚。
“那儿疼吗”我轻声问。
“有点”他说完转过身背对我,做出要睡觉的样子。
“要是你讨厌这样,今后就不这么玩儿了。”
“挺好的,睡觉吧。”他关了灯。
我已经敢肯定,他不讨厌月工茭,只是男性的自尊受到伤害,就象女孩第一次失身一样,或者比那还要难过。我是真心有些喜欢他,月工茭只是一种莋爱方式,尤其在男同性恋中,他懂吗
这男孩太单纯太寡言、内向了。
临近春节,员工的心都散了,我这个老板也没心思工作了。蓝宇几乎每天和我在一起。我没有总和他住在饭店里,太固定的男性夥伴会让人起疑心的,我带他到我在临时村的一套很大的两室一厅的住处。他很喜欢,说比饭店自在。我经常带他玩儿,可那时北京也没有太多好玩的地方,只是在饭店的“迪厅”里,或卡拉ok,打保龄,洗“桑拿” 游泳什么的。我的潜意识里还有个邪恶的念头让他学会享受,向往这些,他就不会再“傲气”了。
他仍然兼着两份学生的家教。他说都是华大老师的子弟,已经说好的,不好意思不干。我不同意他再找其它的工,他犹豫着默认了,他在想什么下学期的生活费吗
再过两天就年三十了,外面的鞭炮零星地响着。他那天还要去一个高三学生家,回来的很晚,他说去邮局给他家里打电话,人很多,等了好久。我很不屑地告诉他无论家里的还是饭店的电话或我的手机都可以打长途。
“我还以为你是孙悟空呢,石头里蹦出来的。”我对他家里的情况很好奇。
他无奈地笑了一下“我母亲几年前就死了,我不想回去,那个女的,就是我父亲后娶的,也不愿意我回去。”
“你爸还好吧”我还想多知道些。
“好,他们一家人都好,我还有个三岁的妹妹呢”他眼睛里又出现那种动人的忧郁,而且深邃,象在回忆什么,但再也没说下去。
大年三十晚上,在我的坚决要求下,他来到我家。这非常冒险,可我真的有些同情他。对这个“我朋友的弟弟”,全家人都算友善。特别是我妈,她对人一向热情,这点我像她,我的两个妹妹像我爸,虚伪,冷漠。蓝宇事后告诉我他没想到我们这种高干家庭也很温馨,我告诉他那是因为老爷子现在失势了,没用了。可他说我应该知足。
快十二点了,鞭炮声四起,我看着小妹,蓝宇还有大妹夫一起放鞭炮,想要是家里人知道我和蓝宇的关系,还不把我给杀了。
第五章
那年一开春就都是好事,先是生意上赚了一笔,又结交了个大人物,将来靠着他一齐做,定是前途无量。再有就是我认识了一个乐队鼓手。
早已经开学了,蓝宇又开始忙,一般两个星期才来找我一次。开学前我将一个两万元的存折递给他,他打开看了一眼
“上次那一千块钱还剩下六百呢。”
“你也太省了,该花钱就花嘛。”停了一会儿我又说
“这钱算我借你的,等你毕业工作后还我,不过可是高利贷啊”我开着玩笑。
看着他有点不情愿的收下,“他妈的,有病”我心里愤愤地骂着。
那个鼓手叫张建,模样只能算还行,可床上的功夫真是一流。他傍上我非常情愿,连我要他先体检的这种无理要求他也欣然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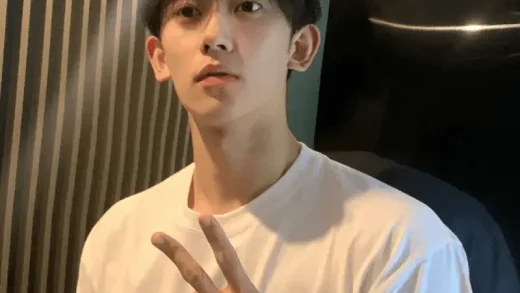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