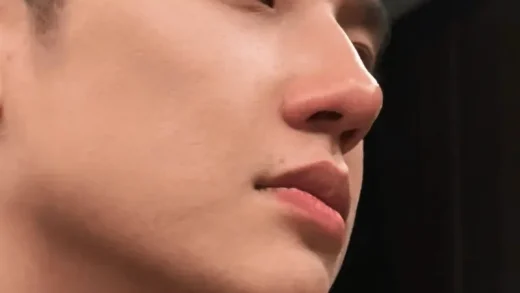在火车站前的大马路上跑了一趟,很棒!机器性能很好,看来这个司机师傅很在意这车,保养得不错。
“今天去哪里?”杨**颐指气使地问。
“塔尔寺。”
“现在路修好了,很好走的,不陪你们啦!”冲我说,拍张辰肩膀。呵呵,心里一定特喜欢张辰。
吃了早饭,驾车上路,百十公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好大一片寺院。人也不多。门前一溜儿雪白的喇嘛塔。购票进门,顿时被这很另类的文化吸引了。古朴的廊柱,雄伟的金顶大殿,金碧辉煌的佛像,陈列在玻璃柜子里的酥油花,满墙的天王壁画——狰狞的嘴脸,威武的气概,骠悍的形象,真是内地寺庙里所看不到的。佛前的海灯是一排排的镀金大碗,火苗摇曳,神气飞扬。善男信女虔诚地磕头,然后把酥油挤到海碗里。
“这就是海灯。你不是看过《红楼梦》吗?里面佛前海灯的诗谜怎么说?”“忘了,我就看情节,不记那个。”
“《红楼梦》的精彩尽在诗文里呀。我过去没看过,你上次说贾宝玉、秦钟什么的,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看完一遍了,是很棒。那里有一首关于佛前海灯的诗谜,是精彩的人生哲理呀。”“是吗,怎么说的?”
“前身色相总无成,不听菱歌听佛经。莫道此生沉黑海,性中自有大光明。”帅哥儿没太听明白,我给他卖弄了一番。这回帅哥儿搞懂了,挺惭愧地连声称赞曹雪芹诗好、方老弟聪明。看帅哥儿一副既钦佩又有点嫉妒的神情,别提多得意了。
转经筒骨碌碌地转动,朝圣的喇嘛披着紫红色长袍,露出一条粗糙的胳膊,围着圣殿,围着寺庙,嘴里诵着经,一圈一圈地转,也有走一步就磕个长头的。张辰学着人家的样子,也挺虔诚地磕了长头,样子又可爱,又滑稽。不过在那样肃穆的地方,没有人会嘲笑别人的。
坐在大殿檐下,听风铃叮叮当当地响,任凉风吹拂,心灵纯净了,透明了。人性变得象刚洗完澡的小婴孩儿,舒服了,吮着手指,看着花花绿绿的世界,小心眼儿里在想:这都是什么呀?
“方,你听这风铃声音多好。”
“风铎!”
“什么?”
“这种大风铃叫风铎。”
“呵呵,是吗。叮叮当当的,把所有的心事儿都抖落干净了。”“帅哥儿,就着这叮叮当当的声音,考考你。”“考什么?又想让我出丑吧?”
“包皮让我翻了不知多少遍了都不觉得出丑,跟人家学点儿东西就出丑啦。知道就知道,不知道一听也就知道了,有什么不好?孔子进太庙,‘每事问’。你比孔子还了不起呀。嘁!”张辰的表情跟寺里壁画上画的天王差不多,揪着我做出痛打的姿势。以此做为对我说翻他包皮的话的有力回击,然后才变成“每事问”的孔子:“你说吧,我猜猜。”“‘镂檀镌梓一层层,岂系良工堆砌成。虽是半天风雨过,何曾闻得梵铃声。’猜猜这是什么塔?为什么刮了半天风雨却听不到风铃的响声?”“没听明白。”张辰如雾里看花,一脸迷茫。
我给他讲解一遍,帅哥儿歪着脑袋瞎猜。
“哈哈,《红楼梦》真的白看啦!看过‘红楼’的人谁都知道呀。”“什么呀?”张辰象没完成作业的小学生似的,狼狈地问。
“有点儿难受,这会儿不说,让**你一会儿。”“是吗?怎么了?”张辰扶着我的肩膀问。
我趴他腿上,把脸埋在他肚子下边。
张辰觉得有点儿不对头,又不好把我推开。“怎么不舒服?”“有点头疼。”
“可能是高原反应。换个地方待着,这石阶多凉呀,风也大。”“不。”我象小猪似地用鼻子拱他哪儿,嗅个不停。
张辰知道上当了,推开我站起来。“不舒服就回去。”“你开车呀?”我翻着眼睛问。
张辰没辙了。
“方,刚才你说那个到底是什么塔呀?我怎么不记得在《红楼梦》里看过呀?”“你尽看秦钟贾宝玉了。”
“没你聪明行了吧?快说是什么?”
“亲一下才说。”我停住脚,把脸一歪。
张辰看周围没人,快速地亲了一下。“说吧。”“松塔儿。”
“什么?”
“笨死了你!就是松果的外壳儿。”
“呵呵,我差点没说是北大未名湖那塔了。”
“怎么扯北大去了?”
“北大未名湖那塔不是水塔吗,没有风铃呀。”“唉!这可真是‘一塔糊涂’了。”
张辰都有点嫉妒了,在我后背捶了一拳:“怎么全让你精了。”“你也不吃亏,傻得可爱!”话音未落,他又给我一拳。
后山有茶座,可以喝酥油茶、马奶。
对这种饮食,张辰都不能接受。我捏着鼻子硬灌了两碗。
张辰小声嘀咕着:“还什么都能喝。”
转悠了半天儿了,该看的都看了,决定回去了。
走到下面,张辰对藏人居住的院落很感兴趣,觉得挺神秘的。我说看看去,他拦着:“别别别,咱也不知道人家这儿的规矩,万一产生误会就麻烦了。”“不会问问有什么规矩呀?入境问俗,入国问禁,入门问讳。不问怎么知道。”我拉起他就走。他虽然不说什么了,但从拉他的份量上感觉得到,他是被我硬拽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