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喝?”
“你先喝半瓶儿我再喝。”
“你等着喝我拉出来的呀。”
张辰更乐了。“你再瞎说人家可喝不下去了哦。”“好,我不说了。你快喝,多喝点儿,一会儿拉出来不臭,能把蜜蜂招来。”“别闹了哦,都三天没有大便了。快对点水喝。”我把蜂蜜里对上麻油,调成蜜水,让帅帅喝。辰辰一边乐,一边喝,心里准在想上次在山里喝蜜的事儿。
我跟妹妹要了个钝针,坐在床边上给帅帅刮脚。帅帅左腿恢复得好,右腿不见进展,只是脚趾、脚面有些感觉,两三天没变化。神经科主任来看过,说可能还是神经有损伤,建议继续输那种营养神经、保护干神经的进口药液。
帅帅一听说“损伤”,心里的沮丧和不爽全写在了脸上了。也不爱说话了。
“看你那样,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呀。再这样我可把你妈叫来啊。”“会不会以后右腿不能动了?”
“刚治疗几天呀,就想恢复成健康人。没听大夫说,康复是个长期过程吗,你已经算恢复快的了。”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忍不住跑到花园里去给中医研究院的那个老专家打电话,把帅帅情况告诉了老先生,并打听可能是什么问题。
“明天我过去看看,把方子调整一下。”老医生挺坦然地说。
25号上午,我去接老大夫。这老先生现在主要是带学生,每周只有两个半天门诊。今天没有门诊,所以上午带着两个学生来到妹妹她们医院。
老人家给帅帅号了脉,然后又让他学生诊脉。三人又把帅帅翻腾着看了一边。
“你们看看怎么处方合适?”老人说。
两个学生赶忙拿处方,凝思片刻,各写一张方子,交给老师。老人接过来看了看,随手放皮包里,说:“处方。”然后一边在窗前度步,一边一味药一味药地随口念出,并随带说出剂量。两个学生赶忙抄方。
“您看问题大吗?”
“处理得当就不大,处理不当就可能有问题。”“那您看这样处理行吗?”
小妹在我后腰上拧一把,低声说:“怎么不会说话呀?”哦,我没意识到自己哪儿说得不合适。
“师爷,我有个问题想请教。”
“姑娘有什么问题呀,尽管问。”老人慈眉善目、温文尔雅地说。
“恕我冒昧,我钻研了您的药方,发现您开药好象没有针对伤情的。”我也在小妹后背上拧一把,低声说:“怎么不会说话呀?”老大夫乐了。“西医是医病,中医是医人。西医针对症状处方,直取病症;中医针对人处方,扶正祛邪,用提升人自身的抗病和康复能力去消除疾病。”“谢谢师爷,明白了。”
“应该说顿开茅塞。”
“少多嘴,你也不怕老爷爷笑话你。”
“哈哈,听口气你们是一家子吧?”
“嗯,他挺聪明的,悟性特好,就是爱买弄,您别笑话啊。”“多精的小伙子呀,准不是大夫。”
“那为什么?”我好奇地问。
“当大夫不用太聪明。当然我说的是中医。学中医的,情商要高,智商一般就行。学西医的,智商要高,情商别太高。哈哈,我瞎说啊,别当真,别当真。”张辰实在忍不住了,说:“您看我还能恢复成以前的状态吗?”“怎么?没信心啦?”
“有你那麽说话的吗?你怀疑*爷爷治不了你的病呀。”我冲张辰说。
“哈哈,这小伙子真是够精的,激将法呀。没问题,就是早好晚好的事,别着急啊,没听电视里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吗?”大家又说笑了一会儿,老人家告辞,我开车送他们回去。
下午,帅帅说肚子里闹腾。我和老商抬起他的两腿,见肛门撑开了,干硬的粪便也看见了,但拉不出来。
“我给你抠出来哦。”
“别跟小妹说哦。”帅帅央求我。
拿小勺的柄,一点儿一点儿地挖。恶臭弥漫了房间,张辰更难为情了,“快把窗子打开吧。多臭哦。”“你怎么那么多顾虑呀,谁拉屎不臭啊。”我亲亲地骂他。
干硬的部分抠出来了,里边的软些的粪便一下拉了出来,再往后是稀的了。换垫子,洗屁股,我和老尚忙活着,总算弄干净了。
“方,我怎么好象感觉到你手在我肛门处摆弄啊。”其实,我们此时并没碰他。
“是吗?觉得我在摸你?”
“哦。可能是错觉。”帅帅也发现,老尚去处理污物,我离他老远,不可能在碰他。
“有错觉也好呀,至少是有感觉了呀。”我赶紧掀开被单,去抚摸他屁股。哇!肛门里又流出黄色稀便,但没什么臭味儿。
“有感觉嘛?”
“你在摸吗?这会儿又没有了。”
看来真是错觉。我又帮他擦屁股。
“方,晚上扎针灸时要是控制不住怎么办?”
“你是病人,控制不住也没人怪你。一会儿我问问小妹怎么办。”晚上扎针时,小妹用纱布卷把帅帅肛门临时塞上了。我给他擦洗干净,喷了点香水。张辰挺难为情地问:“是不是有怪味儿?”“没有。你不是事儿多嘛,所以喷点儿,放心了吗?”帅帅一蹙下巴,挺娇气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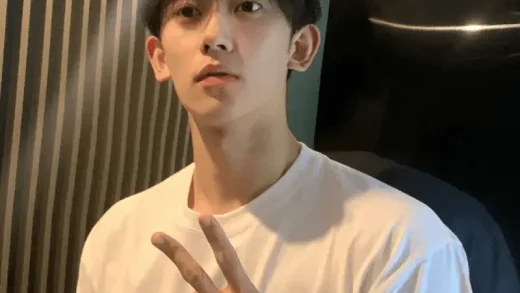

这种感情天上地下绝无仅有,作者的记录手法或者是写作手法挺喜欢,期待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