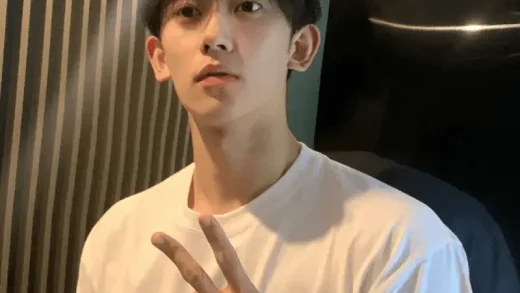过了好久。
他说了一句话:好,我明白了!
说完了之后,他站起来,消失在了夜色里。
我特别想哭,但是我却一滴泪也没落下来,我只是把头埋在我的膝盖上,把嘴里的酒气,统统倾泻到我裤子上的纹理里边。
……哥,我知道错了。
……真的,真的,对不起……
五十六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光哥出来了,他拍了拍我,我抬头看了看他。
光哥小声和我说:走了?人呢?
我用手撑着膝盖站起来,转身往回走,光哥上来扶住我。
我说了一句特没良心的实话,我说,光哥,其实你不应该这个时候把他叫来的……
光哥估计是念着我心情不好又喝了酒,也没怎么把这句话往心里去。
事后想了想,我那天晚上,都做了些什么啊!
——我恨酒!
回到楼上,又喝了多少,我基本就忘了。
我这人喝多了很少吐,一般情况下也很少闹事,往床上一躺,一觉到天亮,爬起来吃碗往死里放醋的拉面,神清气爽,一条好汉在12个小时后涅磐。
这次有些不同,因为喝到后来,我已经没力气做别的事情了,据木头后来说,我那天是直挺挺的被他们给扛回去的,一点神志都没有,据高明及其玄乎地说,我除了还有呼吸和体温之外,和死人没什么区别。
我是第一次把自己喝到这个地步,以至于他们把我扔在床上脱衣服擦脸盖被子等等一切相关事宜,我一概不知。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一度想不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脑袋像被水泥板子砸了一样疼。
小蔡在屋里,他看我醒了,走过来问我,醒了?呵呵,你昨天和谁呀?喝得那么多?
我这才想起来我昨天喝酒了,同时想起来昨天从中午到晚上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我甚至不敢相信这些事情都是我干出来的,和洛基动手如果在情理之中的话,那和我哥,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我昨天说出来的,真的是我的心里话吗?
这时候,光哥推门进来了。
他径直走到我床边坐下,说,怎么样?难受吗?
我笑了一下,说还好。
小蔡问光哥,挺子昨天怎么了?怎么喝了这么多?没见过他喝成这样啊。
光哥说,呵呵,谁能把他喝成那样啊,也就是他自己呗。
没错,我是自己把自己灌醉的。
我觉得昨天那个时候的我,对自己和别人来说,清醒实在是一种折磨。
说到这儿,高明回来了。
我一直特别佩服这小家伙,他好像天生长着两张脸,在寝室外面一张,回到寝室又是一张。
他看到我在屋里,刚回来的时候脸上那副正襟危坐的表情不见了,回到了属于我们寝室的那份熟悉的天真浪漫。
他蹦过来给了我一拳,说你醒啦?昨天你那呼噜打的,我的天哪……你们是不是都没睡好觉?
他扭过头征询光哥和小蔡的意见,他们俩在那儿说其他的事儿,没理他。
高明看得不到呼应,就接着扭过头来说,你看看你,这么大人了还因为这点小事儿把自己搞成这样。
我没说话,这小子装大人的时候最像小孩儿,你这个时候要是理他他准装个没完。
这时候光哥问,高娃,先别说这个,让你办的事儿有眉目了没有?
嗨,我正要说这事儿呢,挺子哥,我刚从导员那儿回来,洛基这小子在那儿泡了一上午,我去了两趟都赶上他在里边,我就没进去,有话不好讲嘛,刚才我再去,他去吃中午饭去了,导员也正收拾着要出门,我就和她一起吃的饭,嘿嘿,人家请得我!
木头说这个的时候一脸眉飞色舞,好像请他吃饭的人是中央领导。
光哥说我没问你这个,后来呢?
后来阿,我们就吃饭了啊,我就和她说,我说徐老师啊,李挺是个特别好的人,思想要求上进平时乐于助人,反正就按照活雷锋那么夸你的,我还说昨天的事是你一时冲动啊,而且也是因为学院的荣誉失去了嘛,说白了也都是为了院里,你看看这处分能不能就算了。徐导听我说完就笑了,她说她知道我就是为这个来的,她还说她知道你。一开始她和我打了一阵官腔,然后说其实处分这事情肯定免不了的,毕竟打了人,又被那么多人看见了,洛基的态度还很强硬,对了,那家伙还说他鼻梁骨被打断让你负责任那,哈哈,真爱秀阿,徐导说其实院里心里有数,但是又不能不给个洛基说法,所以处分免不了。但是她也叫你放心,说警告处分是最大的惩罚了,这两天大四的朴队也一直和她说这事情呢,她也了解了一下,责任不完全在你,最主要的是这两天学校要迎省里的专家检查团,院里当让想大事化小嘛,所以顶多是个警告处分……
说到这儿,我听见光哥和小蔡同时松了口气。
我没有。
我关心的不是这个。
其实从昨天晚上我哥离开我身边那一刻起,我突然间就像失去了灵魂一样,我觉得,似乎什么事,在我这里都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