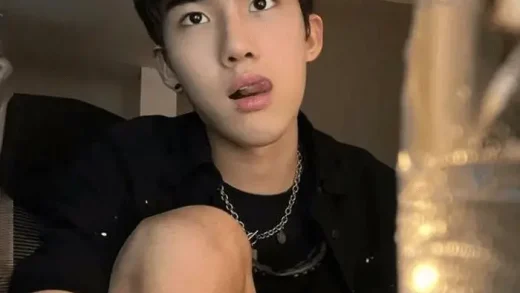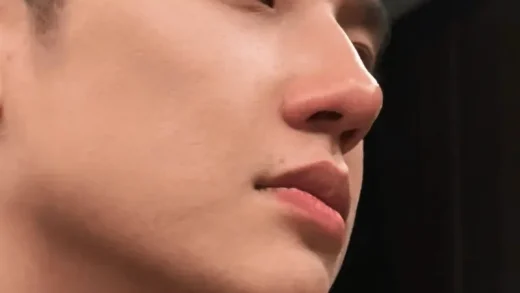因为我们的父母长辈们,是不过圣诞节的。
甚至他们当中有的人,会不知道圣诞节是什么东东。
当然在近些年,许多中年人也开始刻意把这天赋予一些特殊意义,但是他们的兴趣更多是来自他们的子女,而度过的方式也更多的是应景的电话、短信,或者找个地方吃饭喝酒。
吃饭喝酒天天都可以,圣诞节不过是一个名目,和婚丧嫁娶打麻将赢钱单位发奖金一样的名目。
他们不可能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最繁华的地方,他们的孩子们在用自己的热情和快乐,把一个与中国人毫无关系的日子改造成一个节日。
因为,惟有这个节日,说了算的,是我们。
缓慢行动的人群里,干什么的都有。
我拽着我哥买了一大把各种各样的焰火。
我们在人群里把这些由各种各样与磷有关的东西制成的廉价焰火点燃,看着他们放射出红色绿色桔色的光,晶晶亮的火星在空气中牵引出一道又一道的白烟,再坠落到铺着残雪的地上。
在走过一个街口的时候,我突然往人群不太密集的地方拐了拐。
他注意到我的行踪,也跟着过来了。
我突然说,不好了!
他听到我说这个赶快靠了过来。急急的问,怎么了?
在他靠近我的时候,我飞快的点着了一根焰火棒,冲他丢过去。
直接丢在他帽子上。
他愣了一下,我在一旁哈哈大笑。
他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把手里的一根鞭子状的烟花点着,然后作势要抽我。
于是我们把手里的焰火毫不吝惜的一个接一个点着,又毫不吝惜的向对方丢过去。
我们快乐的丢着笑着,笑着丢着,身边经过的人也笑着躲过我们和我们丢出来的焰火,在这样的氛围里,严肃的人是可耻的。
我的弹药是先用完的。
我转身就跑。
他看到我跑,也不扔东西了,在后面追着我跑了起来。
那个时候,时间已经不早了。
这个年龄分化很严重的节日,除了我们聚集的地方之外,其他的地方和普通的也没有区别。
零下20度,除了我们这些精力过剩的年轻人,谁还有这个心情在外面胡闹呢?
所以刚跑过了一个街角,基本就没什么行人了。
他是追不上我的。
但是我没考虑到脚下的冰。
脚下一滑,我结结实实的扎在路旁的雪堆上。
我挣扎着想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
他选择和我栽倒的方式接近的姿势,直接扑到我身上。
嘴里嚷着,我让你跑!
路灯比较昏暗。
偶尔有路人经过,似乎也没太怎么关注我们。
毕竟一个街口之隔的大街上,大伙闹得更欢。
他在这堆残雪上,身下压着的,是我。
喘气……喘气……
他的嘴唇,离我的脸很近。
我能感觉他呼出来的热气。
冬天穿的还是比较厚的。
但那一刻,我还是感到了他身体的温度。
和他的心跳声。
他看着我,眼神里面,似乎也有些东西,在像焰火一样跳动。
我也看着他,我突然觉得,在这样寒冷的季节里,他的眼神,似乎要点燃一些东西。
正在此时,那边传来了三嫂抓狂般的呼唤:老二——!小孩——!你们在哪儿啊?!
……焰火熄灭了……
他把我从雪堆里拉了出来,开始认真地帮我把身上的冰和雪拍掉。
这时候三嫂六嫂领着大队人马到了。
六嫂说,你们干嘛呢?玩摔跤呢啊?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倒是我哥说,呵呵,这小子偷袭我,被我治了。
三嫂依偎着三哥说,老二阿,我可好久没看你这么开心啦!
我哥看了看我,说,是啊,还不是这小子给我闹的。
六嫂接过话茬说,啊,哈哈,原来你有恋童癖啊,我说么,来,到姐这儿来,离他远点,他是变态!
大伙笑了。
我没笑。
他似乎也没笑,我不确定。
我没笑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感她那句话最后的两个字。
虽然我知道这只不过是个玩笑!
十八
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去吃饭。
在这样的夜,大大小小的饭店餐馆各式料理人满为患。
他们寝室的人在喝酒这个领域里和我们寝相比基本不是同一个星球的人。
有人说,去了东北,就是究竟过敏的人也能锻炼出来酒量,这基本上是以讹传讹,因为我一直觉得,酒量这个东西是天生的,只不过有的人之前没开发出来罢了。
或许他们寝室的人都是没有天赋的那种。
倒是三嫂这人看上去满文静的,喝起酒来反倒游刃有余,六嫂虽然感觉上舞舞扎扎的,在酒桌上倒很矜持。
三嫂是齐齐哈尔人。
东北的女生在酒量上都是深藏不露那种,这一点在我大学四年的酒桌生涯里面体会极其深刻。
我只喝了一杯啤酒。
两个姐姐倒是一直在怂恿我。
但是我曾经答应过一个人,尽量少喝酒。
何况这个人在我旁边一直监督我。
还不断地说:行了你俩,人家不会喝酒!
我不会喝酒?我心说,我说我不会喝酒,我妈都得笑话我。
但是我还必须装出为难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