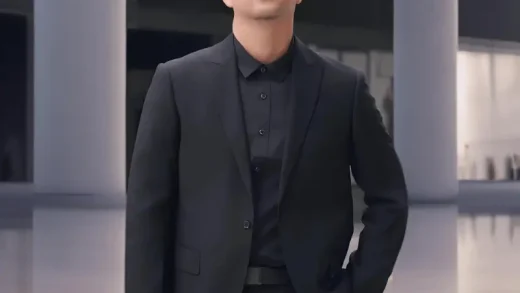看到杨东辉作军旗手的照片,战友们都很兴奋,说排长太帅了。尤其是咱们排的,那种骄傲,出去在二排三排面前都脸上带光。在部队就这样,排与排之间,班与班之间,集体的荣誉感和竞争意识很强。咱排长是阅兵的军旗手,手下的兵个个与有荣焉,这种自豪感真是打心窝子里出来的,24K纯金的。
白洋一听说我回来了,下了纠察哨就冲回来了,他一家伙跳到我身上,我不得不托住他,他居然戴着钢盔就在我脸上吧唧来了一口:“老高!总算回来了,想死我了!”
“操,恶不恶心你?”我把他扔下来,擦了把脸上的口水,他就是属狗的一兴奋就啃人:“还穿着军装呢!注意影响!”
“走了连个电话都没有,真他妈不够意思。”白洋进了宿舍就翻我的兜,看里头啥都没有这小子一脸失望:“你啥都没带啊?”
我哭笑不得:“你当我去逛大街啊?还给你买酒买吃的?”
“不带吃的你回来干啥?”他一句话堵得我想把他蹬出二里地。
他不惦记吃的了,开始关心我的脚了,他听说我脚有伤,非要我脱了鞋看看伤怎么样。脚已经没大碍了,不过我心里有点感动,到底是最铁的兄弟,别人都只看我当护旗手的风光,只有他关心我的伤势,够意思。
看了那些照片,白洋面部表情特别丰富:“老高!帅啊老高!老帅了!”他边咋咋呼呼边拍着大腿,末了搭着我肩膀说:“不过不是我打击你啊,你距离我的差距是缩短了那么一点儿,但是比起你们一排长那差距有点儿大。”
我说:“你前半句说什么?”
他说:“差距有点儿大。”
“前半句。”
“差距。”
一阵惨叫声结束了这段对话,我俩以白洋亲口承认他不是想死我了,他是好一阵没挨揍,欠收拾了,结束了这次亲切友好的会晤。
第二十章
回到军分区,日子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不同的是我和杨东辉的关系。以前刻意的回避,我曾经的自制在阅兵回来后土崩瓦解。也许我早就预感到是这个结果,人最难的就是自欺欺人,放任是饮鸩止渴,然而我已经控制不了了。
自从回来,他的事很多,每天仍不忘到我们班里转转,看看我的脚,提醒班里战友留心。等我能正常训练以后,他也减少了我的训练量,怕我恢复不好留下后遗症。训练时他在队伍前训话,眼光不时和我碰触,那再也不是跳过我的视线,也不是一碰就躲开的回避,我们相视之间有一种不需要说话的默契,他会把目光在我脸上停留几秒,叮嘱一些要领时也会看看我的眼睛,我心底流过一股暖流。
这晚上熄了灯,宿舍里很快响起了鼾声,我没有睡,这一晚是杨东辉查铺。我在床上烙饼,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终于门推开了,一道手电光在各个铺位上照了照,照过我时也没有停留,光线晃了过去,就关闭了。
脚步声并没有离去,而是向我的床头走来,我闭着眼发出轻微的鼾声。他走到我的床前,轻轻掀起我脚上的被子,打开手电看了下伤口,伤口恢复得已经差不多了,他看过后就关了手电,帮我把被子掖好。
他的动作很轻,手碰过我的腿。我故意翻了个身,他拉起被我弄开的被子为我盖上,在肩膀两边掖了掖。这时我睁开了眼睛,他以为我被他弄醒了,低声问我:“冷不冷?”
我摇摇头。
“快睡”他要走了。
“排长”我低低地喊他,他转过身来。
他也瞅着我坏笑,轻声说:“睡不着?那起来五十个俯卧撑!”说着伸手来拽我,我连忙笑着挡住他的手,他胡撸了下我的头顶,“快睡觉”
他走了,我却真睡不着了。 ——
删减内容——
早上出完操,马刚过来贼笑着问我:“昨晚上吃什么大补的了,动静那么大?”
我操,我的脸涨了起来,恶狠狠地说:“你干事没动静?你绣花啊?”
宿舍里半夜整点这动静,太正常了,谁没干过。一群精力过剩的光棍有火只能憋,憋不住了,只能半夜跑个马放个炮。班长有一次下哨回来,以为我们都睡死了,整的那动静地动山摇的,嘴里还出声了,把我们一个宿舍都弄醒了。后来一个兄弟受不了,翻了个身,那声音立马就停了。第二天起来,班长跟没事人似的板着脸训这训那,我们也都很配合,集体装聋作哑。
“那也得有花让我绣啊!”马刚很惆怅。外头遍地是花香,但是一道营院门让我们这些火力强壮的男人只能和自己的右手搏斗。
“哎,告诉你啊,我看见排长也跑马了。”马刚窃笑说他早上去洗手间路过杨东辉宿舍,看到他抱着被子出来,被子上一块地图正好被他撞见,他跟杨东辉开玩笑,被杨东辉一脚蹬回来了。
“那地图画的,好家伙,不愧是排长,火力就是比咱壮啊!”马刚直乐,他当作一件趣事告诉我,却不知道我光是听了他的描述,裤子里马上就有了反应。脑海里出现了杨东辉打枪时的想象,这种想象对我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