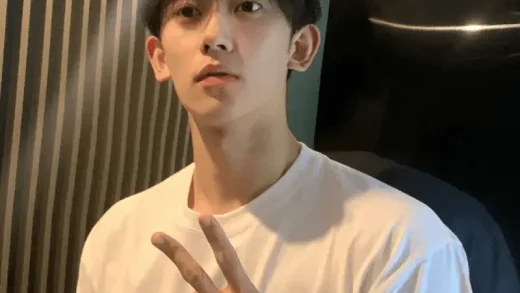一开始还没敢喝,但屋里没开窗户,加上那激烈的人声让我感到焦躁,感觉有点儿热,只好拧开瓶盖,猛喝了几口。
老女人又坐回到沙发里,里屋的声音似乎有意识地压低了,听起来有些遥远,有些奇怪。我想抽烟,摸摸口袋,没有,看了看那老女人,她已经沉浸在电视里了。无事可做,脑袋放空,又开始想韩文珺,他在干吗?之前种种猜测中就只剩下一种想象了,那就是他跟那女的假戏真做,此时恐怕正打得火热。
那奇怪的声音引我胡思乱想,我想象着韩文珺伏在那女人的身上,丑态毕露的样子。毫无预兆地,一股浓烈的酸味从胃底浮起,迅速攒将上来,好在眼疾手快拉过垃圾桶,哇地一声吐了出来。
满屋子冰红茶的味道。老女人只是扭头看了看我,又继续转过去看电视。
没等他们完事儿,我就走了,我是逃出来的。那斑驳的防盗门背后是简直像地狱一样的存在,每一秒都是对我折磨。我大口呼吸着外面的空气,仓促地逃回了家。
临睡时,老姚发过来一条微信,这次不是语言,是文字的。
“明天有啥安排?”他没有问我为什么提前走了,没有提到他们晚上玩的怎么样,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一切都不足以挂齿。
“不知道。”我也回了文字,故意冷待他,对他今天晚上的安排表示不满。
“这季节去西边儿合适,听说草原的草长出来了,开车三四个小时就能到,去吗?明天一早走,晚上回来,过去骑骑马、烤烤羊。”又换成了语音,笑嘻嘻地说。
“跟谁去?”我也回他语音。
“我带我媳妇和闺女去,你也一块儿来吧。”果然会玩儿,转脸就又一副好男人的样子了。
我就这样被掰弯了—韩文珺(二十六)
我有多少年没再想起过住在对面楼上的那个姑娘?那是十四五岁情窦初开时,曾经炽烈燃烧过我的火焰,是我无数个夜晚的终极渴望。居然在即将三十岁的时候,在一个混沌的周日早晨,再一次梦见了她,梦见了那时的自己。
她比我大几岁,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她就已经快要高考了。我不认识她,但我妈大概跟她妈打过几次麻将,算不上很熟,在街上遇见会客气地打声招呼那种。
我猜她学习应该不大好,因为我从来没有从任何人的口中听到过有关她的信息。如果她很优秀的话,她一定会成为我妈以及她的那些牌友们争相讨论的对象,因为全小区的当了妈的女人都在密切关注着小区里别人家的孩子,特别是即将高考的小孩。她们会把这些孩子逐一进行比较,然后争论他们当中的谁能在几个月之后考上大学,谁不能。
她不优秀,应该也不至于太差,因为太差的孩子也会成为焦点,人们总得找个反面的例子作为嘲笑对象。她就像是一个隐形人一样不被任何人注意,除了我。我最开始注意到她,是因为她走路的姿势,很怪,总是弓着腰,半低着头,齐肩的头发滑下来,遮住她的半边脸;她的一只手紧紧攥着另外一只胳膊,看起来有些紧张,似乎在躲避着什么。
我记得她一直穿着那身蓝白条的运动校服,裤子很宽大,上衣也松松垮垮,即使这样,依然掩盖不住她正在蓬勃发育着的身体。她的胸部比别人的都要鼓,她每走一步,胸前都会荡起一阵波澜,剧烈而不受控制。我是在很久之后才明白,那波澜恰恰是她的弱点,是让她感到自卑的原因,她之所以含胸走路,只是不想让人看到她已经发生变化的身体。
我从来没能看清楚她的长相,每次相遇,也只是很快瞥上一眼,而后迅速低下头去,大概还红着脸,局促地擦肩而过。有一次,我终于鼓足勇气,在她面前停了下来,多看了她一会儿,试图看清楚她的眉眼,然而我的眼神却不自觉地向下,停留在她努力掩盖的部位。我的小小举动立刻引起她的警觉,她把头埋得更低些,加快了步伐,为了报复我的不礼貌,还狠狠地踢飞了脚边的石子。
她的这个动作让我很是吃了一惊,既失落又羞愧。尽管努力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在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勇气多看她一眼。
有一段日子,我内心全部的期待就是能在街角或者小区大门口与她相遇。遇到了,迅速错身走过,与此同时,内心猛然生出一种难言的狂喜。品尝着这种狂喜,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冲着上六楼,钻进我的小屋里(我小屋的窗户正对着她卧室的窗户)。站在窗户前,看着她推开她的房门,把校服脱掉,一屁股歪在椅子上或者重重地扑倒在床上。
即使在学校了,见不到她的时候,她那略显微胖的身体,高高鼓起的胸脯以及圆圆的屁股,也同样能时不时地扰乱我的思维,让我无法解答出黑板上那些复杂的函数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