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我立刻把书合上,腾地站起来,慌得我左顾右盼。还好,院子里除了我,一个人也没有。我听见欢声笑语从屋子里传出来。随后我听见田喜的哭声,母亲抱着田喜走到了屋外。
“我带喜儿出去转转。”母亲说道。
“好,去吧。”我说。看着母亲带着田喜走出了院子。我才又怯生生地站在原地背对着屋子把书翻开。快速找到刚才看到的“这坏小子”的部分,继续仔细看。
“你的,如儿子一般的…
即在这里,我的爱使我的心与生命为之欢欣。
这里,他的美眼应允助我,不久目光却移动别处去了。
这里,他和我关连着;
这里他却和我分离了。
这里,我无穷哀痛地哭,
我看见他走了,不复顾我了。”
我被这样的文字深深的打动。这段文字让我想起父亲和我。我的眼泪失去控制流了下来。这是对我心多么准确的诠释。
我停留在如此凄美的文字中,不可自拔。我的心,跟随着米开朗基罗受伤的心一起哭泣。直到我听见有人从屋子里走出来,我才快速地把书合上又快速地走进那间堆放了杂物的屋子。我把这本书放进了木箱里,然后又魂不守舍地走出屋子。
在院子里,看撞到了父亲。
“你一上午都在做什么?”父亲问。
“没,没做什么。”
“你一上午都呆在那个杂物间里?”
我实在想不出那间杂屋里除了那本民国旧书外还有什么可吸引我的。“当然没有,爸爸。”我突然想到了什么,“我只是想找那本《色彩》的书,就是你进城给我买的那本讲绘画技法的书,你忘了。”
“你过去的书我都帮你规整好的。那找到没?要不要我帮你。”
我之所以想起那本《色彩》的书,是因为书里有一副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上面还有一副不记得是那个名家画的人体习作,我清楚地记得画面中一具男体全裸着高举一只手臂背向读者,另一具男体则躺在他的前面。也许我真应该把它找出来。
“好的,爸爸。”
我说。
父亲进了那间杂物间,很快便从那捆整理好的书籍中找到了我要的那本书。
“从小学到初中,还有你小时候临的帖和画的素描稿都在这里。”父亲说,“尊儿走后,我又整理了一遍,你看,这两捆是你的,这捆是尊儿的。”
我看见我那厚厚的两捆书与田尊及其少量一小捆书紧紧地挨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
父亲把他找出来的书交到我的手里。在他转身的时候,我看见父亲用目光扫了一眼旁边的那个敞开的木头箱子。那本《弥盖朗琪罗传》正翘着一个角四平八稳地躺在箱底的一块旧布上。我不知道父亲的目光和翘起一角的一本民国旧书会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但我有一种预感,父亲不希望我读到这本书。那他发现我动了书了吗?他会质问我吗?我像做贼一样窥视着父亲。
一切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父亲扫视完后竟逃一般的往出走。结果在门口,田心抱着几本家谱进来了。
我想是父亲要田心收拾好拿进来的。田心把家谱交给父亲。父亲接过家谱走回到木箱子面前,我看见他掀开箱底的那块旧布,快速地把那本《弥盖朗琪罗传》蒙在了布下,然后把几本家谱摆放在了布的上面,然后又把箱盖向下一拉。在“啪”的一声之后,我看见父亲一脸肃静地走出了杂物间。
父亲走后,我把那本我并非掌握的绘画技法《色彩》打开。读初中的时候,在我的要求下父亲进城买了这本有关绘画技法的书送我。我翻到大卫像的那一页。
我看见愤怒的大卫目视着前方,他身体近乎放松,唯独那双手与它的目光一样充满仇恨地紧绷着。我曾问过父亲,大卫手中到底拿的是什么。父亲说是甩石器,是古代战场上使用的一种武器。父亲说这幅雕塑刻画的人物是一名战士,他在作战休息的时间里,用仇恨目视着前方的敌人,随时都在准备着出击。我说是的,你看他很警惕的样子。其实我心里在想,他和爸爸一样的身材,只是那个JJ也太小太小了。
我又找到那副人体习作。之前我对这样的画面并没有异常的认知,我只是觉得那样的身体和大卫像一样太完美了,但此刻这样的画面不得不让我重新来定义。看着两具赤裸男体一站一躺相互交错回应着,邪恶的我竟然想象出了米开朗基罗和他的侄儿,我甚至想那画面如果是我和父亲。
“看什么呢,这么入神。”田心把脸凑了过来,“哥,你的画家梦又复苏了?”话刚说完,紧接着我就听见我妹 “呀!”的一声惊叫。我立刻把书合上。然后我妹一脸羞涩地扭头跑了。
一个不知道是疯子级的天才还是天才级的疯子,他那对男人甚至包括自己的侄儿所产生了不同常人的感情,让我激动昂扬,心潮澎湃。而这情感原本应该是属于友谊和亲情的范畴。多么荒唐的事情,而我也竟然与天才也好疯子也好的巨人级人物一样的荒唐着。那弥盖朗琪罗的侄儿到底是怎么想的,又是怎么做的。弥盖朗琪罗又是如何自救呢?也许他并非需要自救,他不是说了,愈使他受苦,他愈欢喜。他的悲伤也是他的欢乐,他的欢乐也是他的悲伤。那我呢,我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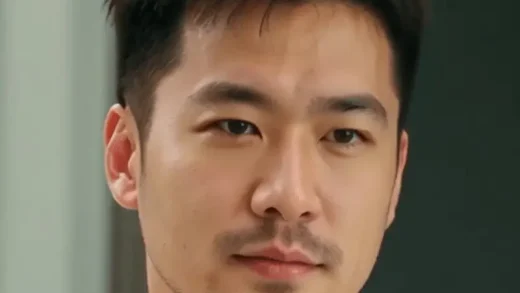


下半部啥时候才有
真的有人看过下半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