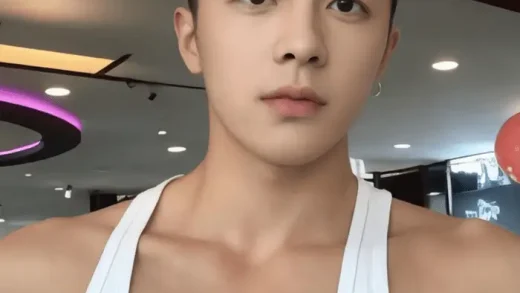最后,我气得连“拜拜”都没有说就走了,气势汹汹地上了车。
那天,我在得出冒菜脑袋里一定是缺根筋这个事实的同时,又确认了一件事——
我大概是一个戏精吧。
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我终于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了我们村口,隔壁张叔家的黑虎用“汪汪”两声迎接了我。
乡音未改鬓毛衰,这句诗说的应该就是……黑虎吧。它依旧是汪汪地叫唤,但是几个月不见,它脖子上的毛已经掉了许多。
乡亲们,我回来了。摸了摸黑虎的头,我正式投入了家乡的怀抱。
回到家的第一天,老父亲老母亲跟我是久别重逢,怎么看怎么顺眼,“儿砸儿砸”声声入耳,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但是,过个两三天之后他们俩就变脸了,跟我变成了相看生厌,怎么看怎么不对。
在家里磨皮擦痒的过了十几天,就要过年了。但过年对于身为大学生的我来说,是一件十分无聊的事情。
你的年纪在那里摆着,不可能跟家里的几个小屁孩一样,放两个烟花爆竹就高兴得欢天喜地的,或者抱着一部动画片能过一整天。
就连伸手拿红包这件事,都显得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但是,你要想出去做点让自己高兴的事情吧,经济实力又不允许,你还没到自己挣钱自己花的份儿。
所以,过年那段时间,我每天除了出去应付七大姑八大姨各种奇形怪状的打探和拷问,更多的时候就是窝在沙发上跟冒菜用手机QQ聊天。
那个时候的流量费贵的要死,5块钱才30M。
你们自己想想,现在30M能干啥,下几张照片的原图,缓冲几首标准音质的歌曲,撑死也就这样了。
幸亏那个时候我们用的都不是智能机,买几个30M挂个QQ聊聊天,省吃俭用的还是可以应付的过去。
我们在QQ上天南地北地胡扯,时间也就打发过去了。
冒菜在网上是比现实生活中还能说的人,他把他小时候的照片拍给我看,非让我选哪一张是最好看的;
他把那只啄过他小鸡鸡的芦花鸡也拍给我看,配文“老鸡伏枥,志在千里”;
他逼着我到他的QQ空间里去浇水留脚印……
总之,有冒菜陪着,我感觉好像也没那么无聊,时间过得挺快的。
大年三十那天早上,我们家团年,一屋子都是人人人人,里里外外忙得团团转。我跟冒菜在QQ上没说几句就下了。
等吃完年饭,大人们都坐在桌上砌长城,小孩儿们被打发出去玩泥巴,我才想起冒菜。
拿出手机登上QQ,但是并没有看到冒菜的信息。可能也是家里招待客人,比较忙,没时间聊天。我没想太多,出去当“孩子王”了。
等到了“爆竹声声辞旧岁”的晚上,春节联欢晚会都快过半了,我仍然没有收到冒菜的任何信息,也没有接到冒菜的电话。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拿手机给冒菜打了一个电话,接通之后却只是听到一阵忙音。
也许,他是跟亲戚朋友出去玩,没有带手机。
我安慰了自己一番,也没有心情看春晚了,在噼里啪啦的烟花爆竹声中,心神不宁地回了自己的房间,盯着手机屏幕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大年初一,按照惯例,我是一定会睡懒觉的,而我妈也一定会一大早就来把我拎起来的。
那天早上,我六点过就醒了,就为了起来看看,手机上有没有收到冒菜的信息。
但是我忘了,冒菜是个比我还懒的人,怎么可能六七点就起床呢。
怕把冒菜吵醒了,我按捺住想立刻给他打一个电话的冲动,而是起床洗漱后,跑到厨房里帮我妈煮汤圆。
我妈惊讶地看了我一眼,惊呼“今天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啊”,然后被我用一颗滚烫的汤圆塞到她嘴里。
结果,当然是换来了一阵母爱的狂风暴雨。
艰难地等到了八点过,我兜里的手机才忽然一震。我赶紧掏出来一看,果然是冒菜的消息。
但是手机屏幕上一个字都没有,只有一张有点模糊的照片,照片里是一条小腿,腿肚子上,一个拳头大小的墨黑色创口异常醒目!
我当时心里就一颤,噼里啪啦打了一句话过去:
“冒菜,你到底怎么了!”
等消息发出来,我多等一秒钟都嫌慢,不及冒菜回答,直接拨了电话过去,也没空心疼异地通话昂贵的电话费了。
“你的腿到底是怎么回事?昨天晚上怎么不给我发消息?现在感觉怎么样?医生怎么说的……”
电话一接通,我就噼里啪啦问了起来。
话筒里一阵沉默之后,才听到冒菜慢悠悠的声音,“号丧啊你,问题那么多,还让不让我说话了!”
号丧……大过年的,我想说蠢货你这么说有点不吉利,但终究还是被他气定神闲的口气给镇住了,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随后,冒菜在给我说了大致情况之后,问了我一个毫无技术含量的问题,“我什么都没说,你咋晓得那是我的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