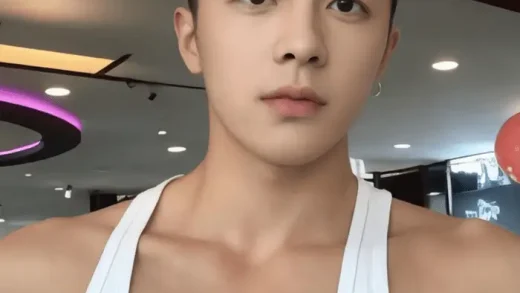冒菜笑骂着了一句滚蛋,把枕头放在我床上,轻车熟路地窜到我床上,把被子裹在了身上,对着我眨了眨眼睛,“寝室有个兄弟来了个朋友,大爷我今晚在你这借宿一晚,如何?”
我笑着说,好啊。心里还有一句话:如果可以,我倒是希望你借宿一辈子,如何?
掰起指头算,冒菜来借宿的次数太多了,用老二的话说,我跟冒菜都是“老夫老妻”了,所以我已经不像当初那么心潮澎湃了,紧张得一晚上都睡不着。
偶尔有点小期待,也会很快就被席卷而来的睡意给取代。
只是,当冒菜习惯性地把手枕在我脖子下面的时候,我轻轻地把他的手放到了被子里。“已经入冬了,天气冷,小心别着凉了!”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是冰天雪地的,老大围着一条白色的围巾,和一个女孩子手牵着手在前面走着,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跟在后面。
他们越走越快,我再怎么努力也跟不上。最后我有点害怕,喊了一声老大,等等我啊。
老大转来头来,我看到的却是冒菜的脸。
那个梦过于真实,以至于我直接被吓醒了。
我满头大汗地睁开眼睛,整个寝室漆黑一片,只有耳边冒菜均匀的呼吸声提醒我,刚刚是一个梦。
我把头蒙在被子下面,本来是想抹去汗水,眼角却没来由的多了一道泪痕。
等情绪稳定后,我才从被子底下下钻出来。侧过头去,我努力睁着眼睛,好像这样就能把近在咫尺的冒菜看清楚。
但是凌晨两三点的夜太黑了,我什么都看不见。
想起梦境里的画面,我心里很慌,脑袋里一片空白,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想,只想靠近冒菜一点,再靠近一点。
脑袋如同在太空中遭受重大变故后脱轨的飞船一样,终于在湮灭于星河之前,被冒菜的呼吸所指引,循着他身上的巨大引力,重回正轨,一点一点向他飞去。
在这寂静地夜间飞行中,我听见发梢在枕头上摩擦的声音,我听见鼻息渐渐交错的声音,我听见体温慢慢碰撞的声音。
这场急速而又万分缓慢的飞行,像走了一光年那么远,虽然目标离我,不过两三个拳头的距离。
最后,我用一个薄如蝉翼的轻吻,宣告我抵达了目的地。
我颤抖着,怀揣着巨大的小心,轻轻地停靠在冒菜的嘴角,像两个人不经意翻身后的挨近。
大概是嘴角的凉意让冒菜有些不舒服,睡梦中的他轻微地摇晃了一下脑袋,随后整个人都缩进被子里。
但是他的手却摸摸索索地伸过来,最后习惯性地扣住我的手,牢牢不放。
这个无意识的举动,轻易地解救了我。我紧紧握着冒菜的手,缓慢闭上了眼睛。
再醒来的时候,天空已经微微发亮。
我发了一会儿呆,挣扎着坐起来,准备去食堂买点早餐回来,却忘了一只手还握着冒菜手里,刚坐起来又给他大力拽了回去。
“大早上的能不能安分点,给我躺好了,我还想多睡一会儿。”
冒菜嘟囔了一句,脑袋就势往我这边靠过来,脸贴到我的肩膀上。
他茂密的发梢很快扫到了我的脖子,不知道是冷还是那一瞬间的触感,让我忍不住起了鸡皮疙瘩。
这样温存的感觉,虽然已经经历过了那么多次,仍然让我贪恋。 我只好又听话地躺下,盯着上铺的床板继续发呆。
冒菜心满意足地把大半个身子挂在我的身上,用手轻轻拍了拍我的脸,继续做他的春秋大梦。
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隔壁老四的床上有动静,转过头去,他已经穿戴好从床铺上下来了。
“老三,你醒了啊,我去食堂买早餐,你……和冒菜想吃什么?”
老四走到床边上,看了靠在我肩膀上的冒菜一眼。
“我随便吃点啥都可以,他嘛……”我有点不好意思,拉起被子盖住冒菜的猪头,低声说:“他不饿,不用给他带,他已经睡着了。”
然后,一个声音就从被子里幽幽地飘了出来,啪啪打肿我的脸:“两个芽菜包子,一袋豆浆,谢谢老四,钱在小安的兜里。”
我:“……”
老四心领神会地笑了一下,走出了寝室。
等老四一走,我立刻掀开了罩在冒菜头上的被子,本来想先骂他个狗血淋头,结果毫无防备地就对上了他那双惺忪眼睛。
他半睁半闭间瞄了我一眼,用手一把勾住我的脖子,把我拉到了他的胸口上,反手把掀开的被子盖了回来。
呼吸一窒。好烫。
那一瞬间,我只有一个感觉,好烫。
不知道是我的脸烫,还是他的胸口烫——虽然入冬了,但是他睡觉是只穿一条内裤的,所以,我的脸是贴在他白花花的胸脯肉上。
如果是以前,我一定会立刻挣扎着爬起来,我的尊严和羞涩的内里都不允许我这样,即便我内心对这种时刻充满了渴望。
但是那一刻,我破天荒的没有动静,只是在滚烫的触觉中,俯首帖耳,安静地倾听他胸腔内平和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