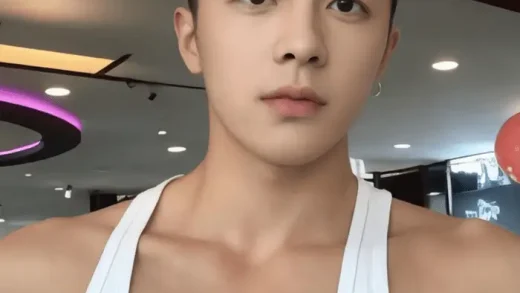我当场石化。
老四听完笑了两声,弯腰把口袋捡起来,摸了摸我的头说:“老三,我刚好要洗衣服,要不我帮你们洗了吧。”
“不用了老四,谢谢你!”
我当然不可能像冒菜那么无耻,还是乖乖端起盆子和洗衣粉,从老四手里拿过那堆臭气熏人的衣服,朝洗衣房走去。
那天,三个人的电影就这样剧终收场。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但是在这场电影里,老四没有姓名。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好的结局,但是我明显感觉到,老四好像已经下了什么决定,他的笑容,他的坦然,他的轻松都回来了。
他看我的眼神重新纯粹起来,没有多余的期待,只是温暖。
这固然让我欣喜,但对我来说,却有一个刺埋在我的心里。或者说,那根刺一直都在那里,只是刺痛越来越明显而已。
后来,冒菜那套衣服洗干净后,我一直没有换回来。
他的衣服我一直留着,毕业后一个人住,有时候夜里我会拿出来穿上,站在镜子面前傻傻地看着,好像站在我对面的人就是他一样。
秋天的早上,阳光迟迟没有驾临,洗衣房里一个人也没有,看起来有些阴暗。我端着盆子站在门口,忽然怔了一会儿。
我想起第一次跟冒菜在洗衣房遇见的时候,我来洗那条拿错的小熊床单,赶巧遇到他也在,被他两句话当面拆穿。
明明应该是尴尬的事情,现在我想起来心里却暖暖的。
因为那天的阳光是真的好,他全身被笼罩在光线里,整个人的轮廓都发着光,把我看得呆了。
后来又一起在洗衣房洗内裤,嬉戏打闹,我一把把内裤糊在他脸上,我们还别扭了好几天。
仅仅是在小小的洗衣房,就有很多关于冒菜的回忆,不断浮现。如果每到一个地方,你就想起一个人,那就叫触景生情吧。
我发现我总能在不同的地方想起冒菜。
在大教室,我想起他陪我去上课,被老师点名叫起来。
在天台,我想起他抽着烟对我说,地上一个人走了天上就多一颗星。
在食堂,我想起他发火摔碗,最后又在楼梯上喂我吃饭。
在君再来,我想起他吃的满嘴都是,还一个劲地说没有吃饱……
好像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我都能想起冒菜。不,其实我明白,跟在哪一个地方无关,而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地方,他住了进来。
而那个地方还在不断扩大,不断开疆辟土,迅速占领我的心脏,我的神经,我的血液,直至我的四肢百骸。
这扇门可能永远为他敞开了,但是,他会在里面住多久呢?
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冒菜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旁边。
“你怎么来了?”
我看着他的样子,一定有点傻,因为刚刚那个问题,我始终调整不出更好的表情来。
“老四告诉我你在这里。把盆子给我吧,衣服我来洗,入秋了,水有点冷。”
说着,冒菜没有看我,直接把盆子端到了水龙头底下,倒上洗衣粉,挽起袖子慢慢搓洗起来。
他眼睛盯在自己来回搓动通红的手上,好像也在想问题,又好像只是在专心洗衣服。
“冒菜,昨天晚上……”
我话还没问完,身后老四急促的声音就响起了,“老三,老大出事了,快去看看!”
“出什么事了!”
我转过头去,看见老四一脸着急。旁边的冒菜也停下了动作,凑了上来。
“具体我也不清楚,刚刚辅导员打电话到寝室,说是在校医院,老二他们已经先过去了!”
我们三人一路火急火燎地赶到校医院时,发现老大整个左手通红一片,手背上冒起了好几个大小不一的水泡,校医正在给他上药包扎。
老二们几个站在一旁,但是老大没说话,只是眼睛盯着右手里一块粉色方巾,傻傻地笑,好像也不知道疼。
还好,看情况问题不算特别严重,但是老大的样子是不是……中蛊了啊?我跟老四都松了一口气,问老二怎么回事。
老二说:“听校医说,老大打水的时候,一个水瓶突然炸瓶了,然后被人送到了这里。”
“是不是水瓶爆炸的威力太大,不仅烫伤了手,还震坏了脑子?你们看,你们老大这样子跟失智儿童有什么区别。”
看到问题不大,冒菜又固态萌发耍起嘴皮子来。我白了他一眼,但是理智上还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老大……老大!”
我喊了两声,老大终于从梦境里醒过来,右手一下攥紧,塞进裤兜了,嘿嘿一笑:“多大点事啊,你们怎么都来了,不就是让开水烫了一下吗?嗨,小事,小事!”
对这个粗线条的东北汉子来说,被烫一下当然是小事。
但是对于我们几个来说,看到神经比指头还粗的老大对着一块粉红色毛巾笑若痴呆,那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老大,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异口同声地威逼。
“吼个铲铲,大惊小怪的,能有啥子事嘛!”
校医是个五十上下的小老头,拿眼睛横扫了我们一眼,眼里全是对小屁孩子没见过世面的深深不屑,然后嘴巴蠕动,吐出来一个惊世骇俗的真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