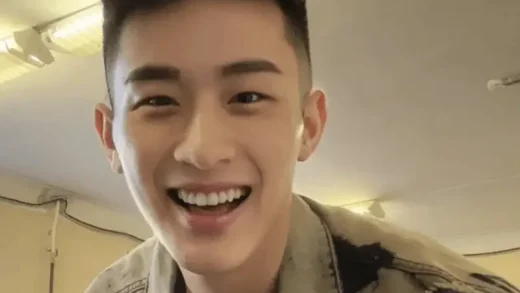那天我大概疯了,前所未有地下着重手,几乎忘记他是我的兄弟了,如果我累了,就停下来抽一支烟,问他:现在呢,做到做不到?我看到蜷在地板上的小广费劲儿地扭过脑袋看我,也许是天大的痛苦在那张惨白的脸上扭曲着,嗓子几乎喊不出话来,但是那越发倔强的目光告诉我,他仍旧在说:做——不——到!
我想我真的疯了。我好像狰狞地笑了一下,缓缓蹲下去,把烟头捻在他袒露的胸口上,然后操起身边的折叠椅子,朝脚下那个抽搐的身体抡过去,一下,两下,……
我想我的胸膛里并没有任何施暴的快感,可手上的动作却似乎成了习惯,就是停不下来了。
如果不是几个兄弟正好过来,把我摁到在地,我想那天小广大概会被我打死。
小广的肋骨断了两根,同时胃出血,在医院里躺了整整一个月。
我当然不会一直疯下去,事实上,当我的兄弟七手八脚把小广抬上急救车的时候,我就已经恢复意识了,前所未有地怕个不停,倒不是怕背负什么责任,而是怕明天会有个身穿白袍的家伙面无表情地对我宣布小广不治。
我几乎退了学,每天都去医院看他,我之所以不是一直守在他的病床前是因为每当看见我,小广就会紧闭双眼,眼泪却突破防线哗哗地往外流,同时还挣扎着去拔自己胳膊上的针头。而小广的母亲如果在,也会哭着骂着赶我走。
小广出院后割了一次手腕,所幸早早被母亲发现了,于是又住进了医院。
再出院后,他跪在地上向眼泪婆娑的母亲保证,绝对不会再有轻生之念。然后他若无其事地找我们道别,说要去深圳打工,我看到他手腕上的伤疤,心如刀绞,我向他认错儿,求他别去,他说他并不怨我,可是绝对不会再听我的。
我他妈的都哭了,兄弟十几个都是第一次见,可小广始终不说二话。于是我打算和他一起去深圳,可是当天晚上就有人告诉我,他已经偷偷离开了家乡……
没有人再获得过关于小广的任何消息,任何人去问他的父母,都问不出任何结果。
54.
真的有那么多直男因为兄弟之上的深情而游离在同性爱边缘吗?不然,为什么只项磊一个人就先后遇见了许梦虎和李增呢?也许这个世界上并没有100%的直男,那些感觉自己离同性爱十万八千里远的男人,大概只是因为没有尝试过兄弟之上的深情罢了。
项磊常常想,如果自己是小B或者小广,大概不会甘心选择离开。可是,如果自己像小B和小广那样离开,裴勇会像许梦虎和李增这样找一个同性恋者倾诉自己有过的兄弟情吗?假如有一天,小B和小广都回来了,许梦虎和李增大概会很快忘记项磊。项磊不禁羡慕起小B和小广来,项磊觉得自己和裴勇的故事比较之下总显得太平淡无奇了,裴勇的情谊就那么停在兄弟情深的高度,一点不少,却也一点都不会多。
李增问项磊何时回家,项磊一想,原来自己已经度过了大学时光的四分之一。李增问项磊暑假时会不会去见他,项磊想了想,说“会”。
项磊告诉许梦虎:暑假回家,我也许会去见一个网友。
许梦虎说:去吧!身为一个同性恋,只被人爱却不被人干,总归不算圆满!
不是听到自己从鼻腔里短促地呼出了一串空气的声音,项磊根本意识不到许梦虎这句话会让自己发出轻笑。
又一个周末的时候,项磊既不待在宿舍,也不去网吧了,而是难得去图书馆借了一本《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扎进主E的自习室里看了整整两天。项磊以为终于躲过了邵一鸣,不料,晚上却接到了他的电话。
邵一鸣告诉魏桐,他帮项磊物色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朋友,项磊一定喜欢,于是魏桐便主动把项磊宿舍的电话号码告诉了邵一鸣。
邵一鸣说项磊我真想你的时候,项磊马上心跳加速,可是项磊对邵一鸣说,好好和魏桐在一起吧,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邵一鸣沉默了一会儿,回道,项磊你真虚伪。项磊忽然苦闷不已,提高音量吼着说:我他妈的也想和你在一起,但想归想,不可能就是不可能!随即,不经思考便挂了电话。
这是项磊第一次当着我们的面儿无所顾忌地说出这些直白的话,我们大概都觉得肉麻,我看见郑东明强忍着不发出声音,夸张地堆了一脸怪异的笑容。
项磊刚刚爬上床铺,电话重新响起,我们都知道仍旧是项磊的电话,所以良久都没人去接。我看到刘冲坐起来找拖鞋的时候,项磊下了床铺。项磊接起电话,皱着眉头粗声喊了一声“喂”,几秒钟内却又和颜悦色起来,随后,项磊扯开电话线,把电话递给了正坐在自己下铺泡脚的郑东明。
郑东明和准女友煲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话粥,刚挂上,就马上又响起了电话铃声。郑东明抓起电话便问:怎么呢?一秒后“哦”了一声,把电话放在铺上,一边说着“项磊,电话”,一边端着洗脚水走出了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