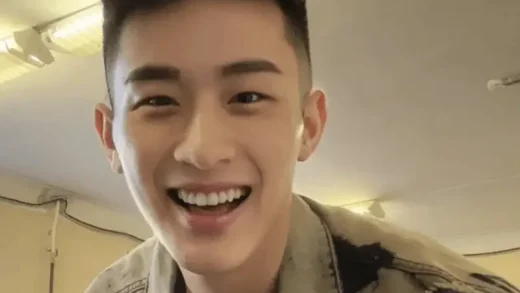何飞听着魏桐这番话,忽然有些夸张地感觉到了一丝悲壮。
“沉重的话题。不如八卦一下你的男朋友吧,怎么认识的?多久了?怎么找了个大连的?见上一面多不容易啊?”
“连他在大连你都知道啊?”魏桐又是一脸惊异的神情。
“也就知道这个了。说说看啊!”
“他单位在北京,新启动的项目在大连,临时抽调过去的。我们在酒吧里认识的,暑假我晚走了几天,去了一趟酒吧就认识了。”魏桐一脸幸福。
这么说,在卫生院里被隔离观察的时候,魏桐还没有男朋友,何飞差点儿把这句话说出来,想了想还是没再提起有关那天晚上的话题。
“他多大了?已经工作了?”
“嗯。26了,都结婚了……”这时候魏桐的脸上闪现出了一丝黯然。
“啊?”何飞张大了嘴巴,不是惊讶于魏桐找了个结婚的男人,而是惊讶于同性恋也会结婚,“和女人?”
“你说呢?”
“他不是……”
“在中国有几个人能洒脱地一直保持单身呢?80%的gay都要和女人结婚,每个人都没办法只为自己一个人活着……”
“那你呢?你以后也会结婚?”何飞看着魏桐,怎么也无法想象出他和一个女人结婚生子的情形来,别说结婚了,连他怎样和一个女生谈恋爱的情形都无法想象出来。
“我?我不会。耽误自己,也耽误别人,每个人都只有一辈子,耽误不起。我想总有办法解决这个决定带来的问题,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最好的办法。”
这时何飞才想到,像魏桐这样用女生的方式漂亮自己的同志毕竟也只是这个少数群体中的更少数,如果项磊结婚,不了解他的性取向的人估计也没什么好张大嘴巴的。
“他和女人……也可以?”
“嗯。再有几个月就当爸爸了。”
看来,这个世界成分复杂着呢。
“对了,我想了想觉得还是有必要告诉你……”魏桐看着何飞的眼睛,好像在提醒何飞要做好某种心理准备似的。
“怎么了?”
“酒吧……那天项磊和我一起去的。有人看上他了。”
何飞当然马上就不高兴了。
“是我拉着他去的,我想去,又不想自己一个人去……我跟你说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你有必要知道,你处理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大概需要这些作为参考。”
何飞想,这个魏桐说话真是隐晦,好像电影台词。
“不过……”他补充道,“那人有朋友,只不过分分合合藕断丝连的,关系不清不楚,我看项磊好像对他也没有特别的意思,也许只是愿意配合地听他倾诉自己的烦心事,把他当成一个好朋友吧。那人约过项磊两次,项磊不好意思拒绝,又怕单独见他会尴尬,每次都硬是把我带上……”
何飞的手机这时候响起了铃声,张雯雯的来电。
“你在哪?干嘛呢?”
“吃饭呢。”何飞随口应道。
“你怎么搞的啊?不是说一起吃的吗?我们在四食堂等你呢!”
“你们吃吧。我不过来了。”
“你怎么能这样?”张雯雯急了。
“怎么样啊?不就一顿饭吗?我正吃着呢!”何飞也开始不耐烦。
然后张雯雯就把电话给挂了。这是张雯雯第一次没有结束语就挂断了何飞的电话。
服务员拿着菜单走过来:“两位要点餐吗?”
魏桐看着焦躁的何飞,正要提议离开,何飞一把抓过菜单,随便点了一个套餐,然后把菜单推给了魏桐。
“不如……回学校吃饭吧?”魏桐说。
“没事,你点吧。”何飞用尽量平静的语气对魏桐说。
魏桐点过套餐,小心地问何飞:“你不会又去找项磊吵架吧?”
“怎么会?我越来越没那底气了……”何飞说。
只有何飞自己知道,表象的焦躁背后其实是隐隐的不安。
篮球赛上的那次意外好像伤到了何飞,当时何飞正用力腾空扣篮,被对手球员冲撞后小腹部感觉到了一种被抻拉的疼痛,尽管过了一会儿明显好转了,可是此后反复无常,偶尔用力就会再次感觉到不适,而且不适的范围在逐渐扩大。10月底的时候,何飞觉得自己的大腿根部越来越不对劲,有时会鼓起一个包,上网查了查,像是得了疝气。何飞叫了表弟一起去医院看了看,医生告诉他的确是疝气,告诫他年纪轻轻不要整天坐在电脑前玩游戏,要常常运动,增强体质。何飞想笑,心想老子每天都在运动,体质没话说。表弟在一旁问医生怎么解决,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手术迟早要做。
一提到要做手术,而且要住院一周,何飞真想骂人。想象着自己完好无损的身体要被那些把自己套在白大褂里趾高气昂的医生戳上一个洞,还没挨刀就已经感觉到了隐隐作痛。何飞倒不是怕疼不起,更让人心烦的是要在病床上躺着闻一个礼拜的药水味儿。
何飞告诉表弟不要对家人声张,他们只会大惊小怪,表弟惊叫道那谁帮你出手术费医药费谁在病床前给你端汤喂饭把屎把尿,何飞面无表情地说道:你。表弟当即表示不干,说自己还有摊子要看,何飞说行,那别手术了,表弟便说回去就通知姥爷,何飞说行,欠的钱不还了,就当探望病人了。表弟哭笑不得骂了一句:你丫真没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