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医生看了一会又把化验单放到桌子上,推了一下眼镜不紧不慢的说:“没是了,是良性的。”
“真的吗?”我一下子从凳子上蹦起来反问道。
老医生笑呵呵的敲着化验单说:“真的,不过……”
得到确认后,我没有等老医生说完就转身跑了出去,抱住站在门口发呆的雨林肩膀大声的说:“良性的,医生说良性的,没事了。”
雨林听到我的话,好像没有反应过来,过了几秒钟才趴到我的肩膀上大声的哭起来,就像受到委屈的孩子有了妈妈的呵护。
我刚才的大喊大叫和雨林的大声哭涕,引来了走廊里的人围观,我使劲拍了雨林后背两下说:“别哭了,这么多人看着呢。”
雨林抬起头擦了一把眼泪,很羞涩的笑着说:“呵呵,我失态了。”
“真是个孩子,一会哭一会笑的。”我也很开心的一拳打在雨林的胸上。
雨林破涕为笑我俩又一起走进了诊室,老医生看我们进来埋怨到:“看把你高兴的,也不等我把话说完就跑出去了。”
“您说,我们认真听着。”我赶紧陪着笑脸很谦逊的坐到老医生面前。
老医生把化验单和病历推到我跟前说:“你们听好了,虽然是良性的,终究是细胞变异,不能大意了,记住一定要回来复查。”
“谢谢您,我们记住了。”我和雨林千恩万谢的告别了医生走出诊室。
雨林是云开雾散心情大好,走起路来连蹦带跳,大热天的一会就搞得自己满头大汗。
“师傅,我想喝冰镇啤酒。”雨林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
“走吧,前面就有一个啤酒大排档。”我很痛快的答应。
在去医院的路上就有一家啤酒大排挡,店家在路边支起了几个绿色的遮阳棚,遮阳棚下摆着白色的桌子和椅子,看起来就很清凉。
还没有到午饭时间,大排档里还没有食客,我们走过去,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立刻迎上来热情的招呼我们。
我俩找了一个靠里的凉蓬坐下来,点了一个熏鸡架和两个拌菜,一人要了一大杯冰镇扎啤。
今天是个艳阳天,天空中满是明亮耀眼的阳光,没有一丝云彩,大有七月流火的韵味。
绿色的凉蓬虑去了太阳的耀眼光芒,营造出一小块清凉的小天地,我和雨林坐在下面,端起冰冰凉的扎啤,大大的喝上一口,淡黄色冰凉的液体通过口腔喉咙食道一直流到胃里,清凉也随之凉爽整个身体,雨林的胃口打开,双手一齐上阵,把熏制成暗红色散发着糖烟熏过的那种糊香的鸡架掰开,挑了一块鸡肉较多的肩胛骨递给我,自己则拿了一块鸡肋,一小条一小条的撕开,然后把一小条鸡肋送到嘴边,津津有味的去啃那上面的一丝鸡肉,鸡肋上的肉吃的干干净净,最后还要使劲把那根细细的骨头嗦上一口。
看着雨林大口的喝着扎啤,精细的啃着鸡架,那个既香甜又享受的样子,我的胃口也被挑逗的大开,酒兴大起,一杯接着一杯的招呼跑堂的小伙上酒。
这是半个月来我俩喝的最痛快的一顿酒,也是吃的最香甜的一顿饭,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偏西,阳光照到了我们脸上。
“不早了,肖霞该着急了”我俩喝的有些忘乎所以,这时才想起肖霞。
我俩醉醺醺的回到雨林家,肖霞看到我俩的样子说:“不用猜就知道你俩喝酒去了。”
“我和你说,今天我和我师傅高兴,真的高兴。”雨林搂住肖霞的大脖子醉意十足的说。
“什么事这么高兴?都喝成这样了。”肖霞说着想拿开雨林的胳膊,但没有成功。
雨林搂着肖霞的大脖子断断续续的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
肖霞听着听着眼泪就流了出来哭着说:“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俩的情绪不对劲,化验单又一直没出结果,我就猜到可能和我的病有关,看你们一天到晚的在我面前装着笑,我也不好意思问,怕再给你们添堵,谢谢你航哥,雨林认识你真好。”
雨林也被肖霞说的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这俩人抱在一起哭,搞得我鼻子也是酸酸的,我拍了拍雨林和肖霞说:“好了,都过去了,就别在这煽情了。”
肖霞抬起头擦了擦眼泪笑着说:“谁煽情了,人家说的是心里话,你俩都喝了不少酒,躺床上睡一会吧。”
肖霞从柜子里拿出两个枕头放到床上,我头沉沉的也没客气,脱了鞋躺倒了床上,雨林也挨着我躺下,肖霞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一觉醒来发现屋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身边的雨林和沙发上的肖霞都不见了。
我坐起来仔细的听了听,厨房有哗哗的流水声和邦邦邦的切菜生,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五点多了,估计是雨林和肖霞在厨房做晚饭。
我下床走到厨房,果然是她俩在准备晚饭,雨林在菜板上切着黄瓜丝肖霞在水池里洗着菜。
“航哥醒了,晚上在这吃吧。”肖霞看到我从屋里走出来主动和我打招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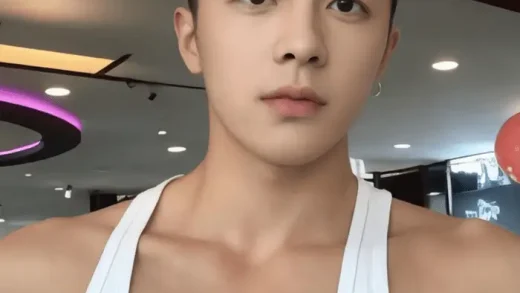
这个前面还有一部,是宇航和林智、杰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