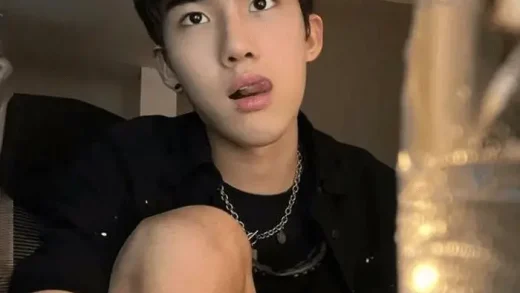“好吧,哪怕一百块一晚,也总得有人照顾。唉,照他这种身体,我看他下半辈子怎么过!”
“姐,那白天的保姆,啥时需要?”杨老板着急地看着徐阿姨,神情有些紧张。
“我先请个两天假,陪着看看。这种开颅的手术,一开始就叫外人来陪,我也不放心,还不晓得手术怎么样,要是不能说话,叫外人来也是白搭。”徐阿姨醒了醒鼻子,刚才肯定流过好多泪水。
“姐,白天就我来好了,你就别请假了。”
“还是忙你的工程吧,你本来就是坐立不安的人,哪里有这个耐心!”徐阿姨态度很坚决,可以看出平日三个老姐弟感情甚笃,做姐姐的也很有权威。
“还是趁手找一个吧,你也伺候不动他,这么重的身子!”杨老板关切地说,又掏出了电话。
“过两天再说吧!”徐阿姨平静地说着,转头看着窗外,身子如泥塑般一动不动。
我轻声告辞,没有惊扰远处媛媛的老爸。
一路惆怅地驱车回家,整个人有点无精打采。老妈和弟弟正在院子里给花浇水,看见我回来,有点惊讶,仿佛发现了一只离群早返的信鸽,还向我身后虚掩的大门看了又看。
“媛媛呢?你没去找她?”老妈着急地问。
“找了,喝了一下午咖啡。”
“噢,是吗?那你没请她吃晚饭?”
“说了,她舅舅突然病了,她要去医院照看。”我轻描淡写地回答,脚步已经踏进了客厅,向楼上的卧室走去。
身后继续传来老妈的问话:“她舅舅?那个做建筑的杨老板吗?”
“不是!”我一边快步走上楼梯,一边敷衍地回答,声音轻得连自己也听不清楚。
可惜了,杨老板!我知道脑溢血是怎么一回事,要是手术不成功的话,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了,即使捡回一条命,也往往会落下半身偏瘫或者部分肌体功能丧失的后遗症。往后的日子,他将怎么去度过?作为一个彻底的同志,没有家庭,没有子女,除了孤独地走完一生,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结局?
一股同情,油然而生。我们温暖的社会大家庭啊,除了雷厉风行地拯救自然灾害之外,为何不给处境凄凉的同志们打开一扇理解包容的天窗?他们平生也在默默回报社会,没有额外制造一丝事端,如果实在不能给予哪怕一点点帮助,就请别再用鄙夷唾弃的目光,去鞭挞他们本已伤痕累累的心灵,逼着他们遁地远藏,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直到天色渐暗,一直还在胡思乱想,终于下了决心,还是给长海叔打个电话,聊个几句。
喧闹的彩铃响过,长海叔愉快的声音传来:“喂,阿清吗?”
“叔,是我!”
“宝啊,你在哪里啊?”
“在家里,叔!你在干啥?”
“没干啥,刚从海滩回来,正准备做晚饭!嘿嘿,你桂芬姐送来一大盆孵房蛋,说是买多了,看着鸡毛又不敢多吃,让我打个牙祭,嘿嘿!”
“叔,那种东西少吃,病菌多的很!”我知道孵房蛋就是小鸡没有破壳之前的精蛋,里面有小鸡,鸡毛,还有蛋黄,看着都有点恶心。
“嘿嘿,你们城里人吃不惯,乡下人就是喜欢!放心吧,煮熟了哪有什么事!”长海叔嘿嘿笑着,我可以猜见他心里肯定在想城里人就是不识好东西。
“那也要少吃一点,叔?”我有点固执。
“好咧,就吃两个,剩下的还给你桂芬姐,就怕她不收,呵呵!”
“叔,你就别逞能了,说不说在我,听不听随你!”我假装真的生气了。
“好啦好啦!叔就少吃几个,你看叔身体壮着呢,老虎都打得死哩!”长海叔俏皮地笑了。
白白的牙齿就在眼前闪过,爽朗的笑声直入我的耳膜。我仿佛看见长海叔那强壮的身体,站在金贵飘香的小院中,肩头挂着夕阳的最后一缕余光,悠闲地踱进踱出,舒展的眉头随着笑声一颤一颤地跳动,被深深的笑纹切碎,消失在慈祥的眼际,而此刻他那粗壮的大手,正举着我精挑细选的手机,和我东一句西一句地瞎扯,甚至故意惹我生气。
一股欲望,从心底火焰般升起,口干舌燥的感觉又涌了上来。长海叔,就算你随意三言两语,也具有如此的吸引力。我已彻底中毒,毒入骨髓,除非把我彻底焚毁,否则无药可救。
我犹豫了一下,决定把杨主席的事告诉他。
“叔,原来你厂子里的工会杨主席,今天出事了。”我停顿了一下,静观长海叔的反应。
“宝啊,你说啥?老杨出啥事啦?”长海叔焦急地问。
“今天下午突然昏倒了,是脑溢血,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良久,长海叔才反应过来,声音很凝重的样子:“咋会得这种病呢?老杨就是不爱惜身子,都一把年纪了,从来不注意保养,咳!”
“叔,老杨到底咋样,现在还不知道,等动完手术,我问清楚了再告诉你。”
“嗯,宝啊,你可要赶紧问清楚,叔明后天一有空就去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