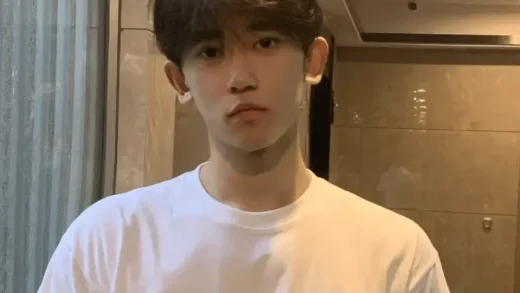有了底气,也就无所畏惧。我拿起餐巾纸擦了擦嘴唇,忍着针刺状的疼痛,冷静地说:“放屁!”
“你说谁放屁?”黄茵茵不依不饶,对我怒目而视。
“谁告诉你的,谁就在放屁。”我固执地辩白,又加上一句:“谁传谣,谁也在放屁。”
气氛瞬间恶化,犹如清澈的水潭里跌落一勺污泥,黑气恣意向水面升腾,在你眼前弥漫。怎么会这样?我不敢抬眼直视黄茵茵此刻绝对犀利的目光,只能盯着眼前铁盘中慢慢冷却的牛排。牛排正变得僵硬,围边的西兰花和洋葱似乎已经冻住了,色泽难看地堆在一起。
“起初我也不信,不过我仔细想过了,事情明摆着,人家能想通就我没想到,空长眼睛却是个瞎子。”过了很久,黄茵茵才开口继续。
“你想过什么了?你除了瞎想还能想什么?还瞎子聋子呢,净胡说八道!”我决定反客为主,结束这次场面尴尬的审讯,就冷冷地顶了一句。
“哼!什么瞎想?人家的眼珠子是白长的,来造你这个谣?我问过,你到江圩去了这半年多,连头带尾在宿舍没住过三天,都是住在那个人家里的,人家一个单身汉,你尽和他挤在一起干吗?还有,你知道别人背后怎么议论你的吗?人家早就把你的事当作新闻来宣导了,你真的没听见?还是自我感觉太好了,当作不知道?”
黄茵茵连珠炮似的责问,情绪激动得甚至有点气喘,说完最后一个“哼”字,把头一扭,转眼看向窗外的夜色,又急忙伸出手,从桌上抽出一片纸巾,想擦擦脸上的什么位置,犹豫了一下转而攒在手里,手臂压住双人座位上放着的一只纸质拎袋,胸脯起伏,勉强自制。拎袋是深灰色的,正面印着一排英文字母,看着非常眼熟,可是我无暇去仔细端详。
脑袋轰然作响。我已经被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自己却没有发觉。恐惧从心底快速升起,胸口一阵疼痛,如利刃在做毫无预警的切割。怎么会这样?这世界到底怎么了?我艰难地呼吸着,似乎空气也成了极端陌生的东西,即将弃我而去。大家在背后议论我和长海叔的事?眼前闪过长海叔憨厚的笑容,他宽广的肩头,强壮的臂膀,站起身如山峦一般巍峨,躺下来如泻湖一般深沉,这就是我愿用生命去呵护的另一个生命,我怎能让他受到诋毁?
曾经无数次臆想,如果长海叔答应和我相守,我宁愿放弃一切,放弃令人艳羡的职务——如果我的选择会给职务抹黑,我宁愿做个底层的小办事员,在碌碌无为中度过余生;我甚至可以放弃公职——如果我的举止不再适合在政府部门工作,有损公务员的形象,我可以辞职下海,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找一个不起眼的位置,聊以填饱肚子;我甚至想到了强忍眼泪远走高飞——即使长海叔不愿同行,只要长海叔不受到伤害,只要长海叔不担负任何世俗的谴责,只要留住父母的脸面,我宁愿孤独地远行,离开这座伤心地城市,走出很远很远,直到父母很老很老的时候,再偷偷地回来,尽自己迟来的一份孝心,那时已不再引人注意,往事已不再被人提及,或许那时长海叔也已经很老很老了,佝偻着身子在江边踟蹰,看云散云起,观潮涨潮落,我就站在他的身边,搀扶着他日渐削瘦的手臂,回忆芦苇花的岁岁枯荣,细数滩涂上的陌生新绿,在满眼金黄的夕阳里,书写生命的最后几页日记。
可是现在,我已成了大家的笑柄。大家都说了些什么?说我举止不正常?说我心理不正常?还是说我根本就是个GAY?我艰难地猜测着,不敢直面向黄茵茵打听。打击来得如此之快,简直来不及作出抵抗的准备,虽然在心重如铁的时候,甚至想过拼死相争,以自己的无畏,换取大家的宽容,我就是个GAY又怎么啦?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耽误任何事,我只是有这种心态,而只有这种情感寄托才会让我感到幸福,感受到此生的价值,这只是我自己的价值,没有强加于人,甚至长海叔,我也只是在默默地守候,守候这一份机缘,就算最终他不愿意付出,我也不会强求,我只是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感受欢容,进行一场没有观众的演出,轻叹,清唱,没有累积别人的痛苦,没有任何人必须做出牺牲,以成全我的另类追求。
我突然明白,所有的坦然都只是一厢情愿,即使投降,也照例会被押赴刑场。当初为何没有细想,所有可能的结局都是失去一切,那么,我为何还要傻傻地坚持开场?我仿佛看见同事们鄙夷的目光,盯着我示众般袒露的背影,父母心头的疑问变成了铁证,然后是一轮又一轮高压洗脑,严局从关爱变成无奈任凭刀俎蹂躏鱼肉,亲戚们窃窃私语交流挽救方案,而丑闻一旦利索地装上翅膀,在会在这个躁动的小城里到处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