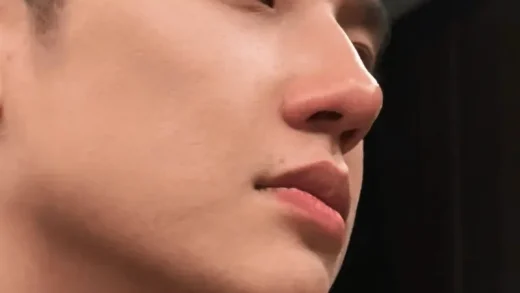“严局,我还是先走吧,我有点急事要办,陪李科长吃饭还是安排别人吧!”我鼓起勇气,坚决推辞。
“什么事情?”严局摘下眼镜,继续盯着我看。
忽然感到有点慌乱,怕自己虚弱的内心被他鹰隼般锐利的眼光看穿。
“一点小事,必须赶回去处理一下。”
说完,我急急忙忙离开,担心稍一犹豫最终会败下阵来。
一路飞驰,直奔江圩。跑出拥挤的市区,驶上笔直的省道,才腾出手再次拨打长海叔的手机,这次终于打通了。在等待接听的间歇,我一直在揣测东东的事端。估计是经济问题,我隐约看出他是个花花公子,世道物欲横流,他早已深陷其中。
“叔?”
“嗯?”
“叔,你电话怎么一直打不进啊?你到底是在跟谁通话讲了老半天?”在问正事之前,我先排解心中的疑问,以免一直纠结不下。
“噢,是和东东的亲妈在通电话!嗨呀宝啊,这个老太婆难缠得要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了半天就是不肯挂电话。”
又猜错了。
东东的老娘哭什么?哭自己管束无方?哭东东辜负教养?还是凄凄切切想用悲情打动?肯定肯定,肯定又在打长海叔的主意!我不免有点担心,忙问道:“叔,那东东老妈又哭啥?”
“她又能哭啥?嗨呀,宝啊,你咋问这么多哩?”
“问问又不会少啥!好啦好啦,叔,我在路上正赶来,大概过半小时就能到江圩,叔你在哪里?”
为了证明我正在开车,我故意连续按响了汽车喇叭。
“噢,你在路上呀?那叔想想……要不叔去你分局门口?”
“好吧,叔,分局门口见!”
我挂了电话。长海叔怎么变得优柔寡断了?去分局门口还要想想,真不知道他要想什么。
一路风驰电掣冲到江圩,远远望去分局门口,哪里有长海叔的影子?再仔细看,进进出出只有车子,没有行人。
可能去我办公室里了。我暗自推测,打了方向盘,准备拐进去。突然,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急急地从马路对面的农业银行里跑出来,手里还拎着一个塑料袋,鼓鼓囊囊的,看上去挺沉。
是长海叔!
只见他小跑着闯过马路,在分局门口站好,然后向里张望,又转过身子,这才发现了紧贴着他停下的帕萨特。
“叔,你慌慌张张急啥?”我按下车窗,看见长海叔把塑料袋藏到了身后。
“不急不急,叔是怕你等急了!”
“叔,那就去里面说话。”
我一脚油门先把车开了进去。终于回到到办公室里坐定,给长海叔泡茶。长海叔微微喘着气,神色有点紧张。
“叔,东东出啥事了?”我把茶杯递给长海叔,着急地问道。
长海叔没有喝茶,反而站了起来:“出啥事了?她娘哭了半天,也没说准是啥事,听上去是说东东这败家子伸手拿了单位里的公款,本来想等年底发了提成自己补上,没想到公司提前查账,被财务告发了,今早才被派出所带走了。嗨,这个败家子,我就知道他不学好,早晚会有这一天哩!”
“噢!”跟我判断的基本一致,“叔,那东东拿了单位多少钱?”
“十二万多。”长海叔伸出两只手指头,在我面前晃了晃。
“十二万?他贪污这么多钱用来做啥?”我吃了一惊,这么一大笔钱,他拿着竟然不烫手?
“别提了,还不是买车!上次来我这里要去了五万,左凑右凑不够,就伸手拿单位的钱哩!嗨,这都什么世道了都!”长海叔说完,坐回沙发上唉声叹气。
“叔,你不是告诉我只给了他三万吗?”我尖酸地挖苦了一句。
长海叔,我知道你给了东东五万,但是东东并不满足,甚至怀恨在心。从送他去车站那一路上怨恨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根本就没有把你当做恩重如山的父亲,在他眼里,你只是一条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吃的是草,积攒的是钱。在我眼里,东东就是一只寄生的牛虻,厚颜无耻地吸食你的鲜血,定期榨干你的积蓄,这种逆子,要之何用?难道寄希望他帮你养老?简直笑话一桩!等到榨干你的鲜血,他又会飞向另一个宿主,把你弃之敝屣。
“我说给了他三万?没有吧!好像我说的是五万哩!”长海叔嘴里低声辩驳着,装作喝茶,看起了杯底的茶叶。
“算了算了,随便你给多少,反正是你的钱。叔,你说现在咋办?”
看着长海叔硬着头皮狡辩,我气不打一处来。你去护短吧,你去溺爱吧,你去给他做牛做马吧!就因为他是你没有良心的养子,你这辈子就要套上终生的桎梏?
“宝啊,叔想和你去趟上海,行不?”
“去上海?去上海看守所看他?”我一脸震惊。
“不是去看守所哩!他娘托人问过了,要是赶紧把钱退出去,案子是可以撤的,也就今天一天的时间,早点动身还来得及哩!公安局那边都在催了,说是积极退赃,可以免除的。”长海叔吞吞吐吐说完,偷偷看看我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