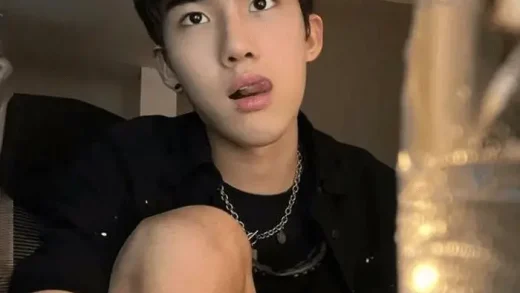“叔,这衣服刚好合身,你穿着真精神!”我赞誉了一句。
“衣服好价钱也贵哩!”长海叔一边扣着袖口,一边回答。
看着地上包好的几件行李,我没有犹豫,赶忙说:“叔,我送你到江圩吧!”
“诶,现在还早,叔就去车站坐大巴。这雪下这么大,你回去开车要多加小心哩!”说完,长海叔走到窗前看了看楼下,远处草坪上已是雪白一片。
“叔,这雪还没结冰,地上不滑开车没事,看你大包小包的咋走?还是我送你回去!”我执拗的坚持,不由分说把长海叔装着脸盆饭碗热水瓶的大网兜提在手里,打开门走了出去。
“宝啊,别麻烦了!”长海叔嘴里还在推辞,见我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得拎起剩下两个提包,跟了上来。
在后备箱放好东西,回到车上坐定,我一边点火,一边扭头瞥了瞥长海叔。长海叔坐在边上,搓着粗壮的手指,鼻孔里喷出一股股热气,深邃而晶莹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前方雪花曼舞的草地。
“看啥哩?”注意到我在看他,长海叔回过神来,咧嘴问道。
“没看啥。”我胡乱应付了一句。
但是那熟悉的气息一阵阵扑鼻而来,心情虽然如负重疴,却渐渐涌起了一丝久违的舒坦。
“叔,老杨走了,你别太伤神了。”驶上马路,觉得气氛沉闷,我挑起了话题。
“唉,我还真以为他睡熟了!老杨也怪,白天睡觉安静得很,晚上才打呼噜,早知道说什么也要去叫醒他的!”
“叔,你别去瞎想,医生说这种病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脑子里的血管都烂了,没法救。”我忙安慰道。
“想通了倒也没啥,就是人在我手里走掉了,我怕他姐弟两个背后说闲话,唉!”长海叔往后坐直了身子,心事重重地回答我说。
“怎么会?叔,他姐弟两个对你感激不尽,你别折腾自己了,嗯?”
长海叔没有回话,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人这一生啊,说慢就慢,说快就快,都是阎罗王掌握定数,定数一到,说收走就收走,没有半点商量余地,嘿嘿!”说完,发出一声苦笑。
“叔,你又在瞎说了!”
“宝啊,叔讲的就是实话。人呐,好不容易来世上走一遭,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看有些个人就是欲念太强,啥都想得到,啥都想去争一回,其实呀,到头都是一场空哩!”
我无言以对。车行荒野,雪花密密匝匝地扑向挡风玻璃,似乎夹带着湮灭一切的声势,天空灰暗,万籁俱寂,树木的枝桠如浣妆的舞女,悄然隐没雪中,留下影影绰绰的身影,捉摸不定。放慢车速,打开车灯,车子如一条不慎从枝头掉落的蠕虫,缓缓地在雪地里爬行。一直没有打开音响,沉静的气氛厚积成白霜,心头却把曹操的《短歌行》一遍遍吟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或许我此生无谓的欲念太强,才会一天天感慨去日苦多?可是,如果不再追逐明日的希望,我岂不枉为朝露,白活一场?
突然有点心神不定,还是忍不住想说上几句。
“叔,老杨这几天有没有谈起过我?”我勇敢地看了看长海叔,仿佛他最初的表情,才是他内心的真实反应。
“说起过,说起过好多次哩!”长海叔砸吧着嘴唇,恍若被我从冥思中唤醒。
“哦?他都说了些啥?”我一鼓作气问道。
“噢,说了好多好多哩!说你有知识,有本事,说你脾气好,心眼好,嘿嘿,这些叔早知道,还用他告诉?”
长海叔看着我,脸上有了神采,似乎我原本就是他的骄傲。
“瞎讲,叔!”我故作羞愧。
“哪里瞎讲!老杨一有精神就夸你哩!”
“叔,老杨还说了些啥?”
“就这些,没啥了。”
“怎么可能?他肯定还说过啥的!”我觉得自己心里好着急,声音也变得好大。
“没说啥,他都说些啥啦?”
长海叔没有想出所以然,有点手足无措,仿佛我是老杨指派的老师,正在对他进行艰难的考试。
“没说就算了!”心里变得有些气鼓鼓的,话也生硬了,似乎断定长海叔刻意隐瞒了最重要的答案。
“没啥了呀?哦,老杨一直要我好好待你,把你当儿子,亲生儿子,要我照顾好你!嘿嘿,宝啊,你看他说的,叔早就把你当儿子养了哩,还用得着他来关照!”
“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切入正题。老杨肯定说到点的,我不会怀疑。
终于,我鼓起勇气,深情地说:“叔,你知道吗,我真的爱你!”
“傻话,哪里还有假的?”
支起双耳,揪心地等待长海叔说下去。但是没有收到任何讯息。
“叔——,算了,我不说了……”
突然感到没有必要继续。多想问一句:长海叔,你也是象我爱你那样爱着我吗?我可以预见你的回答:当然,宝啊,我也爱你!但是我知道,你的爱,肯定和我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