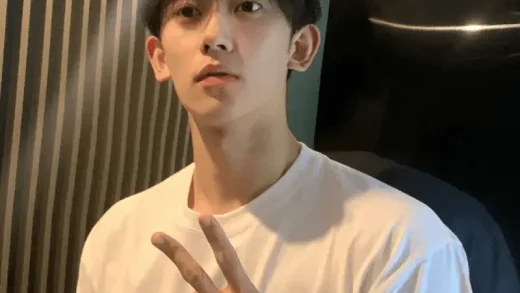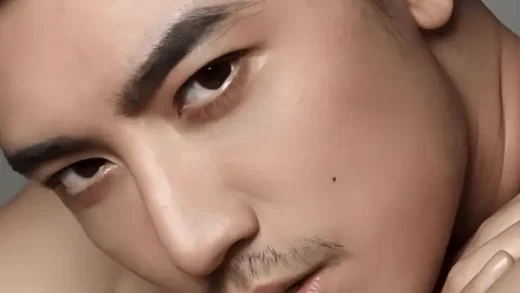“宝啊,你咋啦?”看着我一脸混沌,长海叔走上前来,揉揉我的肩膀,仿佛要将我从梦中唤醒。
就这样站在我面前。胡子拉碴,满脸憔悴,微微发红的眼睛,眼角的皱纹很深,似乎瘦了一圈,鬓角没有修理,短短的发脚在向下延伸,弯弯斜斜地贴在松弛的皮肤上,然后我看见了几根白发,似乎一夜生成,煞是苍凉。
我无动于衷,身子随着长海叔的摇摆微微晃动。
“宝啊,别难受,人总有这一回,别想太多了。”
长海叔面对面站着,盯着我看,一脸的担心。
“叔!”
我突然觉得无法坚强,双手猛地搂住长海叔的肩膀,泪水如雨后的激流,夺眶而出。长海叔壮实的身体撑住我的重量,手掌轻轻拍打我的后背,我的脸深深埋入他的脖颈,如迷途的驯鹿,寻找着最后的家园。
“宝啊,别哭了,别哭,叔知道你难受,老杨只是叔的一个朋友,你不用太伤心,想想别的,过一阵子就好了。”长海叔把我紧紧搂住,一迭声地安慰我。
“不是,叔,老杨是个好人,叔!他太苦了,你不知道的!”
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猛地挣脱长海叔的怀抱,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向他说明,仿佛一头受伤的猎豹,在维护最后的正义。
长海叔的眼神闪过一丝吃惊,随即又把我搂紧,嘴里忙改口说:“晓得晓得,宝啊,叔晓得老杨是个好人,叔没说他是坏人,好人一路平安,来来来,别哭了,让人家看见了不好哩!”
“有什么丢脸的,叔!我去送送老杨!”说完,我转身就走。
“别去!”长海叔一把将我抓住,死死不放手,“你去哪里?太平间里都是死人,那么脏的地方你不能去!”
“就看一眼!”我固执的脾气又上来了。
“不能去!你不能去那种地方的!宝啊,你硬要去,明年叔带你去上坟,你要陪他说说话都可以!今朝不行,你妈知道了会把我骂死的!”长海叔伸出双手把我两只手腕紧紧抓住,捏得生疼,这么粗壮有力的手臂,我如何挣脱?
正僵持间,杨老板突然走了进来,眼睛已经哭得血红,看见我在,就跟我打了个招呼。
“阿清也在啊,刚到的?长海叔你把东西都收拾干净了?”
“嗯,医院说铺盖回收了要烧掉的,其他没用的都扔了。”
“这样吧,现在时间还早,你就坐班车回去吧,今天乱得狠,我就不送你了,大后天出殡,你看有时间就上来吃碗豆腐,对了,我哥哥家里你认得吗?”
“认得认得,我自己去。”
“嗯,这里是4000块钱护理费,我姐说多给你1000块,这回辛苦你了。”
说完,杨老板把一叠杳好的人民币递到长海叔面前。
“哪有这回事哩!这钱我一分钱也不能收!老杨帮了我不少忙,陪陪他也是正理,哪有收钱的说法哩!”长海叔嘴里说着,身子往后躲开了。
杨老板一愣,仿佛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哪能不收钱?嫌少了还是怎么的?”
“杨老板,这钱我肯定不能要!”
看着他俩不停的推搡,我走上前去,从杨老板手中接下了钱:“这样吧,我代长海叔先收下了。”
“那好那好!我先走了,灵车刚到,我还要去带路。”杨老板说完,一阵风似的走出了病房。
短暂的静默过后,长海叔幽幽地开口说道:“宝啊,你给叔收下这钱干嘛?叔哪里能心安?”
我两眼看着空荡荡的床铺,面无表情地说道:“叔,这钱我自有安排,你放心吧,叔!”
我要交给陵园的花匠,在老杨的墓地种满金黄的万寿菊,那重重叠叠厚实的生命,会在老杨的每一个忌日,凌寒怒放,一片绚烂!
”
“ 默默地站在窗前,看着窗外一片白色的世界。风好静啊,刚才还凌乱的飞雪,似乎突然有了纪律整理了队形,以相同的角度,一朵朵齐刷刷向窗口飘来,轻轻地挂上玻璃,恍若在向里面张看,瞬间又融化了棱角,纤细的身姿被玻璃整个粘住,从雪白变为透明,化为半滴水珠,无声地蛰伏着。后面的雪花继续飞来,水珠开始汇聚,终于结成一滴硕大的眼泪,流淌而下。
心头微微一颤,莫非这美丽的生命,也赶来为老杨送行?可惜飞雪晨露,虽然纯美如水的灵魂,终究只能与风霜为伍,一旦旭日高照,短暂的生命即告结束。为何这等瑰丽的精灵,却无缘戏谑风尘,如我一般?
身后变得安静,看来长海叔已经收拾妥当。我转过身去,只见桌子床架擦得干干净净,光彩如新。
“宝啊,叔要赶回江圩去,你也回家去吧!”长海叔边说边穿上一件藏青色的羽绒服,麻灰色的毛领在灯光下闪烁着钻石般的光泽。
我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我给长海叔买的吗!原来长海叔早就随身带着,却一直藏在行李箱里,不舍得穿。长海叔穿着真是太合身了,柔软而不臃肿,挺括而不僵硬,整个容光焕发,光彩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