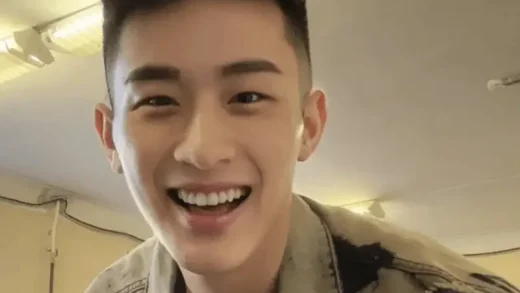“你住回凯兰花园了?”张哥忽然问。
我惊讶的看他一眼,他话题跳的太快,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那个小伙子是不错,”张哥呵呵笑,“可他是结婚的人了。”张哥正经看我,这段时间以来,张哥没再跟我制造两个人和一张床相处的机会,他似乎在刻意保持什么,我也不知他身体上的事是怎么解决的,也不想问,也许他太忙了,就不会有要求吧,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一直以为他还不知道我跟林的事,看来这些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我想继续说小皮跟阳杰谈判的情景,但事情回忆起来有些凌乱了,自助餐厅真不是谈话聊关键话题的场所,太安静,钢琴声像在催眠,每个人都有格调的低声说话,安静进食。小皮连一片烤肉、一滴饮料都没沾,他一直压低声音在辩解,哀求,发誓,要不是我极力制止恐怕又要流泪了。
阳杰表现出与其外貌不相符的镇定和决心,或许这与他当老师的职业有关系吧,眼里有些容不下沙子。那场“谈判”进行了三个半小时,当服务员暗示我们他们要打烊了,我们才匆匆结帐出门,出到餐厅外面有几辆的士体贴的闪着灯,一直向我们召唤。阳杰坚定的说了句:“好和好散,就这样吧!”然后钻进一辆薄荷青的的士,留下我和小皮怅然的立在马路边,白痴一样傻立着。
“刘志还会来找小皮的,”张哥像是要安慰我,“他上次离开武汉时就一直打听他消息,问他喜欢什么,还问他婚姻状况,刘志没结婚。”
我听完忍不住想笑,但又笑不出来。张哥忽然看我手腕空空,有些疑惑的愣着。
我意识到他在注意什么,连忙笑了笑,喝了一口冰凉饮料,说:“放在家里,没舍得随便戴。”其实我是不敢戴。
“没什么,”张哥没说话,他真的有些变了,和从前不同,莫非结婚和离婚真能改变一个人?我禁不住又想到林,人都是在变吧。
和张哥喝东西一直到将近十点,两人好象很久没这样聊天了。张哥把他知道的一些奇闻逸事告诉我,许多都是我从本地报纸上才能看到的一些人物,张哥说起这些来,绘声绘色,井井有条,每个人都像活灵活现。忽然发现,张哥平时话不多,真到说起故事来,却是一套一套的。
张哥又一次开车送我到凯兰花园,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了。车到小区门口停了,张哥没下车的意思,倒是我主动问他是不是要上去坐坐,张哥笑着摇头,说时间不早了,明天还有一大堆事。
不知他是真的忙,还是有意跟我玩技巧,我却很欣赏他这一套,我笑着下车,进小区时回头,皇冠车已经掉头上了马路。
132
我开始喜欢这种全新的关系,与张哥,他似乎对身体要求免疫,尽管偶尔会拍我腿,摸我手,甚至有过亲我嘴的打算,但没有再次深入过,有时反是我要主动,他却借口推托。说起来有些莫名其妙,有时我自己也嫌自己够贱,但我总觉得道德观和价值取向都是空话,人如果过于违背自己的喜悦委身所谓规范,反而显得不真实。
从七月底到八月初,林完全是被动状态,每次我主动联系,他都有万千借口,偶尔一起吃饭,都是他一贯的沉默,我竭尽所能的寻找话题,他竭尽所能的沉默。我有时候会厌烦,真不知道喜欢他什么。
但我还是胜不骄、败不馁的一次又一次约请他,总会有成功的时候,或者在住处,吃个饭,心情好时还有饭后节目,林对身体要求不是太频繁,但我能感觉他已经喜欢这东西了。有时候可能出于健康考虑,没有紧要。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用“三角恋”来形容我当时的状态,但有时我感觉这样的定义并不实际,或者称之为“多角恋”,但觉得“恋”字有些像是在笑话我。人真是奇怪,总喜欢把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归纳为某个状态,这样的定义或许在某些方面为人带来方便,但有时却让人煞费脑筋。
林的婚后生活显然不大幸福,尽管他一直在履行丈夫的责任,他的怨气却一直让我心存恐惧。本来我对婚姻还是有些向往的,以前他一再介绍小娜时,我甚至也有过冲动。尽管不太相信法律的东西,但在外面生活漂泊的久,就会时不时的想要安定一些,回家有人准备好饭菜,有人帮忙烧好水洗澡,睡觉前有人陪伴聊天,心情好或许还能有个孩子,这样的生活,有时我确实是向往的。
林却像反面教材在教育我,也难怪后来他不再热衷于制造机会给我和小娜(当然主要还是我抗拒的原因)。林仿佛一直在提醒我婚姻可能付出的代价:随时有人提醒换衣服,要求洗碗拖地,做事之前要求戴套,或者你不想做的时候也要表现出很想要的样子,因此总要担待一些勃起障碍的风险。不仅如此,还有对方的父母,亲友,过年过节是不停的来回拜访,应景的笑和谈天,记住每个外甥或侄女的名字,岁数,切忌张冠李戴。不能随便上网,更别提成人网站,工作偶尔加班应酬,必须随时报告,解释。还有孩子,尽管林没法告诉我有了孩子会乱成什么样,但就他目前的想象来看,他潜意识里已经把孩子的到来看成一场灾难。